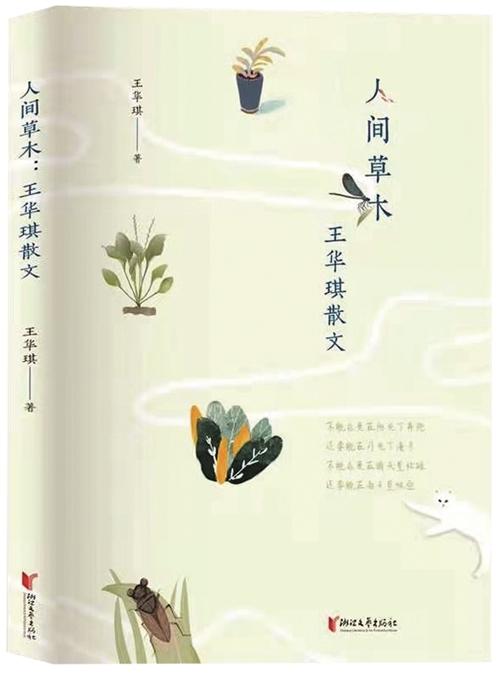洪治纲
董桥说,文字是肉做的。真正的文字,总是发乎情,流于思,是从生命里渗透出来的,犹如河蚌,滴泪成珠。读这样的文字,就像两三好友,围炉夜语,海阔天空,虽不一定有深刻的哲思,但分享的愉悦却妙不可言。
读王华琪的文章,我便有这种感受。他的文字,轻快晓畅,随性而发,虽未见纵论天下之雄心,亦不觉顾影自怜之感伤,字里行间,渗透了一个文人的诗意情怀,也洋溢着作者的人生智慧。见微知著之中,处处彰显其难能可贵的“初心”,宛若雨后空山,清新异常。
有经曰: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是真性情,也是真赤子。一个热爱文字的人,守住初心,便守住了自己的灵魂,守住了精神的小园地,也守住了文章的纯静。文贵乎真,失去了真诚,自然也就失去了文字应有的魅力。
无奈的是,红尘滚滚,太多的人常常深陷功名之焦虑,饱受利禄之诱惑,以至于初心渐失,谋术附身。即使偶作文字,这类人也多半是言工辞巧,别有卖弄。以我的阅读经历,此类文字并不少见。但王华琪的文字,却明确地拒绝这种俗世之气,看似不为,实为不屑。读他的文章,我每每看到他那骨子里的文人气息,敏捷,赤诚,多思,善感,悠然看事,从容论人,不弃“初心”。
拥有一颗“初心”,其实也便拥有了一种从容而独特的写作姿态:为内心的自由,为无序的思想,为灵魂的独语,为存在的诘问。这是一种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写作,也是一种自省自足、力避喧哗的写作。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篇章,均是如此。它们篇幅短小,一律着眼于微观生活,或由古及今,或由物及人,或从乡村到城市,或从景象到时节,娓娓道来,饶有意味。
在王华琪看来,“人生不能总在阳光下昂奋地奔跑,还需要能在月光下漫步的机会;不能总在晴天下忙碌,还需要有这么个雨天放空自我。”(《夏至雨》)这恰如王小波所言:“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以我之见,所谓“诗意的世界”,并不都是那些幻想的世界,不染人间烟火的彼岸,它同样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成为我们对抗现实的一种重要手段,像月下漫步,临窗听雨,都是心灵漫游的绝妙方式。王华琪所渴慕的,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人生境界。所以,他特别希望生活能够不时地“慢”下来,在“慢”中“学会用双眼端详一粒种子的发芽,一个蚕蛹的蜕变,一朵鲜花的绽放;学会用双耳聆听鸟鸣的唧啾,花草的瓣颤,清风的呼吸;学会用双足去丈量菜花的金黄田埂,去触碰田野里麦穗的沉淀……”(《声声慢》)。对于人生而言,这样的“慢”,其实已不是一种生活姿态,而是一种生存哲学,因为它承载了生命内在的超然与自足。
事实上,收录在这本集中的文字,大多体现了王华琪对诗意世界的不自觉的向往、临摹和建构。譬如,面对门前村后到处都是的车前草,他从“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说起,再到欧阳修和韩愈之诗句,旁征博引之中,展示了一种平凡而又超然的生命伦理(《采一株车前草》);行走在深寂的冬天,他却饱含生命的情致,徜徉在冬天的树与水之间,回味着心灵的空阔与寂寥,感受到“冬天的故事很苍茫,但不苍白”(《冬天的故事》);他写故乡村落的旧景,从石屋到小巷,让记忆不时地流淌出无数的宁静与纯朴,以映衬现代文明对诗意生存的消解(《古村、老房子及其他》)。读这些文字,我们仿佛看到作者远离尘嚣的姿态,也可以领略到他那回归本源的“初心”。
这种“初心”,尤为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时节的迷恋性表达上。或许是久居都市,模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王华琪对时节的更替才变得特别敏感。譬如,他对秋天就有着格外的迷恋。《秋日读秋日》《在杭州,请在秋天叫醒我》《杭州点秋香》《秋风鲈鱼催人归》等等,都是抒写秋的感受,并从秋的沉静中寻思人生的况味。在那里,里尔克的诗,琦君的文,钱塘的莼菜鲈鱼,乃至杭州的一叶一花,都会成为他体察人生的窗口,并最终“咏叹出一个季节的旖旎”(《在杭州,请在秋天叫醒我》)。同样,他对江南的雨也有着别样的钟情。《春夜,一场江南雨》《夏至雨》《夏夜里,那一穗宋朝的灯花》《最美人间五月天》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沉浸在江南的雨季里,要么怀想,要么沉思,甚至希望时空能够穿越,“邀请一穗宋朝的灯花,来照亮在自己寂寞的夜空”。
事实上,无论是追忆儿时的成长,还是品味心中的典籍,无论是直面当今的教育,还是旁观时尚的文化,王华琪总是从容淡定,徐徐道来,一如琦君的散文,“素手掸红尘,静心观世俗”,求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赤子的心志与情怀。他常常沉浸在那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里,并从这些日常生活的皱褶里发现意想不到的光泽——就像一个关注内心生活的人,穿行在世俗的伦理中,总希望能够不时地仰望星空,使生活成为一种审美的存在。
如果要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种写作,实质上就是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尽管人们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以为,它的核心指向,应该是将审美的、诗意的态度引入俗世的现实生活,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负载更多的艺术品性,并致力于让美学向日常现实领域延伸与播撒。真正的日常生活,不只是简单的形而下的生存,它还应该包含审美的诗意的存在。这些“彼岸”的存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于那些关注内心质量的人来说,却是须臾而不可离。
倘若用这种理论来认真地审视一些创作,我的感受是,很多江南的文人都可能是这方面的实践者。——不用往远处搜寻,看看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就可以想象江南的才子们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孜孜以求。在那里,作者可以从每一个日常生活细节中,品味到美妙的人生意趣。如果再读读李渔的《闲情偶寄》,尤其是其中的“饮馔部”“居室部”“种植部”,我们可以认定,李渔几乎就是一个行为艺术家,他将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上升到了审美的高度。细品王华琪的文字,说实在的,确有几分旧时江南文人的这种底色,也不乏某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冲动。
这种审美化的冲动,固然会受到某些地域文化的浸润,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恪守初心,从不舍弃一个文人对情怀和理想的抚摸。古人云:“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现代化的都市,总是带着欲望的面孔四处招摇,但对于王华琪来说,在内心深处留着“春余”的底色,也算是人生拥有了一种别样的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