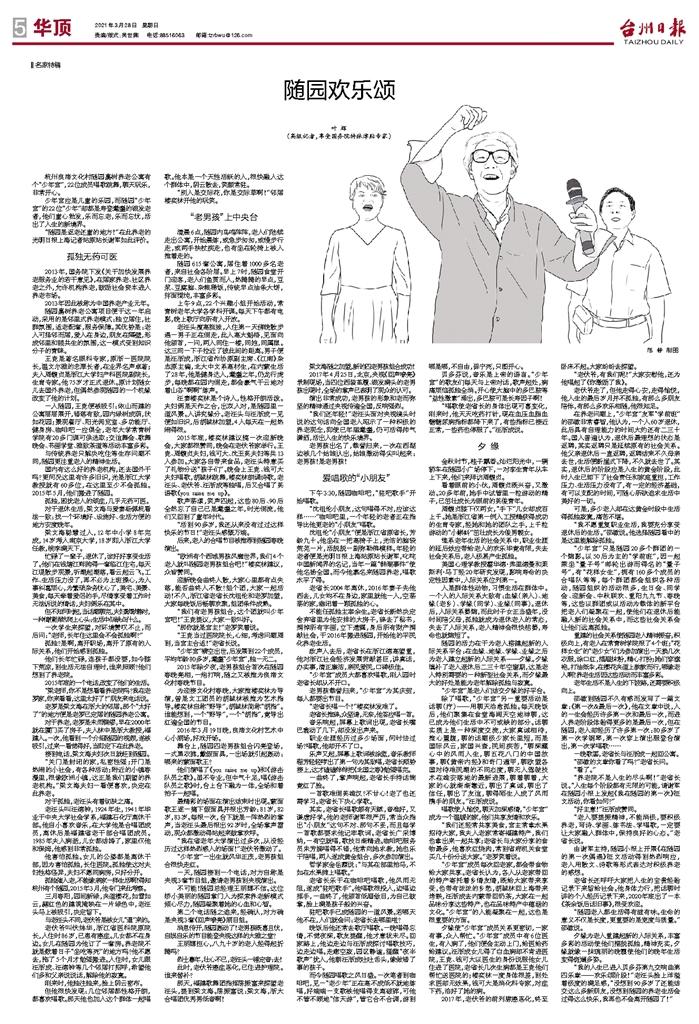𝄃
叶 辉
(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杭州良渚文化村随园嘉树养老公寓有个“少年宫”,22位成员唱歌跳舞,聊天玩乐,非常开心。
少年宫应是儿童的乐园,而随园“少年宫”的22位“少年”却都是寿登耄耋的银发老者,他们童心勃发,乐而忘老,乐而忘忧,活出了人生的新境界。
“随园是返老还童的地方!”在此养老的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原站长谢军如此评价。
孤独无药可医
2013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在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之外,允许机构养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市场。
2013年因此被称为中国养老产业元年。
随园嘉树养老公寓项目便于这一年启动,采用的是邻里式养老模式:独立居住,社群氛围,适老配套,服务保障。其优势是:老人可择邻而居,爱人在身边,朋友在隔壁,形成邻里和睦共生的氛围,这一模式受到知识分子的青睐。
王竞是著名眼科专家,原浙一医院院长,温文尔雅的忠厚长者,在业界名声卓著;夫人周馥贞是浙江大学妇产科医院副院长,生育专家。他75岁才正式退休。原计划随女儿去国外养老,但偶然参观随园的一个机缘改变了他的计划。
一入随园,王竞便被吸引:依山而建的公寓层层展开,错落有致,园内绿树成荫,状如花园;景观餐厅、阳光阅览室、多功能厅、健身房、咖啡吧一应俱全,老年大学常青树学院有20多门课可供选取;交谊舞会、歌舞晚会、书画学堂、雅致茶道等活动丰富多彩。
与传统养老只解决吃住等生存问题不同,随园更注重老人的精神生活。
国内有这么好的养老机构,还去国外干吗?更何况这里有许多旧识,光是浙江大学教授就有60多位,在这里至少不会孤独。2015年5月,他们搬进了随园。
孤独,困扰老人的顽症,几乎无药可医。
对于退休生活,梁文海与爱妻杨佩杭看法一致:找一个环境好、设施好、生活方便的地方安度晚年。
梁文海聪慧过人,12年中小学8年完成,14岁考入南京大学,18岁即入浙江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
忙碌了一辈子,退休了,该好好享受生活了。他们在钱塘江畔购得一套临江住宅,每天江堤散步观景,听潮起潮落,看云起云飞。工作、生活压力没了,再不必为上班操心,为人事纠葛烦心,为繁琐杂务忧心了,美宅、美景、美食,每天牵着爱侣的手,尽情享受着工作时无法诉说的情话,夫妇俩乐在其中。
但不知何时起,当话题聊完,夫妇默默静对,一种情愫悄然爬上心头:生活中似缺点什么。
一次学生来探望,对环境赞叹不止,而后问:“老师,长年住这里会不会孤独啊?”
孤独?是啊,离开职场,离开了原有的人际关系,他们开始感到孤独。
他们长年忙碌,连孩子都没要,如今膝下荒凉,到生活无法自理时,谁来照顾?他们想到了养老院。
2015年底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梁老师,你不是想看看养老院吗?我在老罗家,你来看看,这里太好了!”朋友来电话说。
老罗是梁文海在浙大的邻居。那个“太好了”的地方便是老罗已定居的随园养老公寓。
对于养老,老罗是未雨绸缪,早在2000年就在厦门买了房子,夫人林中是浙大教授,福建人。一次,他看到一个介绍随园的视频,遂被吸引,过来一看觉得好,当即定下在此养老。
接到电话,梁文海夫妇次日就赶到随园。
“关门是封闭的家,私密性强;开门是热闹的小社会,有各种活动;附近的小镇春漫里,很像欧洲小镇,这正是我们期望的养老机构。”梁文海夫妇一看便喜欢,决定在此养老。
对于孤独,老汪头有着切肤之痛。
老汪头叫汪德钟,1924年生,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福建石化厅离休干部。他自小喜欢音乐,在大学他是合唱团成员,离休后是福建省老干部合唱团成员。1985年夫人病逝,儿女都结婚了,家里仅他和保姆,他感到非常孤独。
他害怕孤独。女儿的公婆都是离休干部,因为害怕孤独,长住医院。孤独使这对夫妇性格怪异,夫妇不愿同病房,只好分开。
孤独催人老,不能像亲家一样生活啊!得知杭州有个随园,2015年3月,他专门来此考察。
三月春阳,园间新绿,夹道樱花,如雪如云,赭红色的建筑掩映在一片绿色中,老汪头马上被吸引,决定留下。
与老汪头不同,老伏爷是被女儿“逼”来的。
老伏爷叫伏纬华,浙江省医科院原院长,入住时86岁,已患有癌症。儿女都不在身边。女儿在随园为他订了一套房。养老院不就是数着日子“坐吃等死”的地方吗?他不愿去,拖了5个月才勉强搬进。入住时,女儿跟汪浙成、汪德钟等几个邻居打招呼,希望他们多和父亲说说话,解除他的寂寞。
刚来时,他独往独来,脸上阴云密布。
但他很快发现:几位邻居都性格开朗,都喜欢唱歌。那天他也加入这个群体一起唱歌。他本是一个天性活跃的人,很快融入这个群体中,阴云散去,笑颜常驻。
“别人是交际花,你是交际草啊!”邻居楼奕林开他的玩笑。
“老男孩”上中央台
清晨6点,随园内鸟鸣阵阵,老人们陆续走出公寓,开始晨练,或急步匆匆,或慢步行走,或两手扶杖疾走,也有坐在轮椅上被人推着走的。
随园615套公寓,居住着1000多名老者,来自社会各阶层。早上7时,随园食堂开门迎客,老人们鱼贯而入,热腾腾的早点,豆浆、豆腐脑、杂粮稀饭,传统早点油条大饼,拌面馄饨,丰富多彩。
上午9点,22个兴趣小组开始活动,常青树老年大学各学科开课。每天下午都有电影,晚上歌厅向所有人开放。
老汪头瘦高挺拔,入住第一天傍晚散步遇一男子正在倒走,此人高大魁梧,见面向他颔首,一问,两人同住一楼,同姓,同属鼠。这三同一下子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男子便是汪浙成,浙江省作协原副主席、《江南》杂志原主编,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在内蒙生活了28年,他是健身达人,耄耋之年,仍龙行虎步,每晚都在园内倒走,都会豪气干云地对着山谷“啊啊”练声。
汪妻楼奕林是个诗人,性格开朗活泼。夫妇俩是天作之合,出双入对,是随园里一道风景。人讲究缘分。老汪头与汪浙成一见便如旧识,后胡毓林加盟,4人每天在一起热闹得很。
2015年底,楼奕林建议搞一次迎新晚会,大家都很赞同,晚会在老伏爷家举行。王竞、周馥贞夫妇,钱可大、沈玉英夫妇等共13人参加。大家各自带来食品,老汪头特意买了礼物分送“孩子们”。晚会上王竞、钱可大夫妇唱歌,胡毓林跳舞,楼奕林朗诵诗歌,老汪头、老伏爷、汪浙成等独唱,后又合唱了英语歌《you raise me up》。
歌声荡漾,笑声四起,这些80后、90后全然忘了自己已是耄耋之年,时光倒流,他们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活到90多岁,我还从来没有过过这样快乐的节日!”老汪头感慨万端。
后来,老人的合唱节目被推荐到随园春晚演出。
“欧洲有个西城男孩风靡世界,我们4个老人就叫随园老男孩组合吧!”楼奕林建议,众皆赞同。
迎新晚会曲终人散,大家心里都有点失落,能否曲终人不散?组个团,大家一起活动!不久,浙江省老省长沈祖伦和老罗加盟,大家每晚饭后畅聊欢聚,组团条件成熟。
“我们有老男孩组合,这个团就叫少年宫吧!”王竞提议,大家一致叫好。
“那你就是宫主!”老罗笑着说。
“王竞当过医院院长,心细,考虑问题周到,当宫主合适!”老省长说。
“少年宫”横空出世,后发展到22个成员,平均年龄80多岁,耄耋“少年宫”,独一无二。
2015年除夕夜,老男孩组合首次在随园春晚亮相,一炮打响,随之又被推为良渚文化村春晚节目。
为迎接文化村春晚,大家推楼奕林为导演,曾是文工团员的胡毓林被推为艺术指导。楼奕林自称“野导”,胡毓林简称“胡指”。谁能想到,一个“野导”,一个“胡指”,竟导出红遍全国的节目。
2016年3月19日晚,良渚文化村艺术中心小剧场,好戏开场。
舞台上,随园四老男孩组合闪亮登场,一式黑衣裤,戴假面具,一出场就引起轰动:哪来的蒙面歌王?
他们演唱了《you raise me up》和《游击队员之歌》。虽不专业,但中气十足,唱《游击队员之歌》时,台上台下融为一体,全场和着拍子一起唱。
最精彩的场面在演出结束时出现。蒙面歌王逐一摘下假面具并报出芳龄:81岁,82岁,83岁。每报一次,台下就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当老汪头最后报出92岁时,全场掌声雷动,观众都激动得站起来鼓掌欢呼。
“我在省老年大学演出过多次,从没经历过这样热烈感人的场面!”老伏爷激动了。
“少年宫”一出生就风华正茂,老男孩组合很快走红。
一天,随园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央视3套节目组,邀请老男孩到央视演出。
不可能!随园总经理王丽娜不信。这位娇小美丽的随园掌门人为探索养老新模式倾心尽力,随园凝聚着她的心血和心智。
第二个电话随之追来,经确认,对方确是央视3套《回声嘹亮》剧目组。
消息传开,随园轰动了!老男孩既喜且忧,自娱自乐的节目能登央视这样的大雅之堂?
王丽娜担心,八九十岁的老人经得起折腾吗?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汪头一锤定音:去!
此时,老伏爷癌症恶化,已住进护理院。谁来替补?
那天,福建歌舞团指挥陈振富来探望老汪头,提到梁文海。陈振富说:梁文海,浙大合唱团优秀男低音啊!
梁文海随之加盟,新的四老男孩组合成功!
2017年4月25日,北京,央视《回声嘹亮》录制现场,当四位西装革履、银发满头的老男孩出现时,全场的掌声已表明了观众的认可。
演出非常成功,老男孩的形象和老而弥坚的精神通过央视传遍全国,反响强烈。
“我们还年轻!”老汪头面对央视镜头时说的这句话向全国老人昭示了一种积极的养老观念,即使已年届耄耋,仍可活得帅气潇洒,活出人生的快乐境界。
老男孩出名了,载誉归来,一次在西湖边被几个姑娘认出,姑娘激动得尖叫起来:老男孩!是老男孩!
爱唱歌的“小朋友”
下午3:30,随园咖啡吧,“驻吧歌手”开始唱歌。
“沈祖伦小朋友,这句唱得不对,应该这样……”咖啡吧里,一个年轻的老者正在指导比他更老的“小朋友”唱歌。
沈祖伦“小朋友”便是浙江省原省长,芳龄九十。他坐在一把高椅子上,光洁的脑袋荒芜一片,活脱脱一副弥勒佛模样。年轻的老者便是光明日报上海站原站长谢军,叱咤中国新闻界的名记,当年一篇“韩琨事件”使他名扬全国。而今他慕名来随园养老,唱歌水平了得。
老省长2004年离休,2016年妻子先他西去,儿女均不在身边,家里就他一人,空荡荡的家,幽闭着一颗孤独的心。
不能任孤独主宰余生。老省长断然决定舍弃省里为他安排的大房子,辞去了秘书,捐掉所有字画,立下遗嘱,身后所有财产捐献社会,于2016年搬进随园,开始他的平民化养老生活。
政声人去后,老省长在浙江德高望重,他对浙江社会经济发展贡献甚巨,讲真话,办实事,清正廉洁,亲民爱民,口碑极佳。
“少年宫”成员大都喜欢唱歌,刚入园时老省长却从不开口。
老男孩载誉归来,“少年宫”为其庆贺,每人都要出节目。
“老省长唱一个!”楼奕林发难了。
老省长推辞,众坚请,无奈,他答应唱一首。
音乐响起,屏幕上歌词出现,老省长嘴巴翕动了几下,却没发出声来。
职业生涯经历过多少场面,何时怯过场?唱歌,他却开不了口。
乐声又起,屏幕上歌词被涂蓝,音乐教师程芳轻轻哼出了第一句为其助唱,老省长顺势接上,这才磕磕绊绊把《北国之春》勉强唱完。
一曲终了,掌声响起,老省长手持话筒竟红了脸。
一首歌难倒英雄汉?不甘心!老了也还需学习。老省长下决心学歌。
其实,老省长唱歌颇有天赋,音准好,又谦虚好学。他的老师谢军很严厉,常当众指出“小朋友”这句不对、那句不妥,而且每学一首歌都要求他记牢歌词。老省长广采博纳,一有空就唱,歌技日渐精进。咖啡吧服务员朱芳娣唱得不错,他常向她求教,她也乐于陪唱,两人遂成黄金组合,多次参加演出。
哲学家金岳霖说:“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老省长乐于在咖啡吧唱歌,他风雨无阻,遂成“驻吧歌手”。他唱歌很投入,边唱边挥手,一曲终了,他颔首低眉敛目,为自己鼓掌,脸上满是孩子般的兴奋。
驻吧歌手已成随园的一道风景。若哪天他不在,人们就会问:老省长去哪里啦?
晚饭后他还常去歌厅唱歌。一晚唱得忘情,不觉夜深,歌友提醒,他才意犹未尽。回家路上,他边走边与汪浙成探讨唱歌技巧,边走边唱。走廊空寂,园区静谧,猛醒“夜半歌声”扰人,他朝汪浙成吐吐舌头,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而今随园唱歌之风日盛。一次笔者到咖啡吧,见一“老少年”正在高不成低不就地练唱,好端端一支歌被他唱得支离破碎,可他不管不顾地“信天游”,管它合不合调,游到哪是哪,不自由,毋宁死,只图开心。
贝多芬说,音乐是上帝的语言。“少年宫”的歌友们每天与上帝对话,歌声起处,病痛烦恼孤独全消。开心使大脑中的多巴胺等“益性激素”涌出,多巴胺可是长寿因子啊!
“唱歌使老省长的身体出现可喜变化,刚来时,他天天吃药打针,现在血压血脂血糖糖尿病指标都降下来了,有些指标已接近正常,一些药也停服了。”汪浙成说。
夕 缘
金秋时节,桂子飘香。灿烂阳光中,一辆轿车在随园小广场停下,一对孪生青年从车上下来,他们来拜访周馥贞。
看着眼前的小伙,周馥贞既兴奋,又激动。20多年前,她手中试管里一粒游动的精子,已茁壮成长为眼前的英俊青年。
周馥贞膝下仅两女,“手下”儿女却成百上千。她是浙江省第一例人工授精获得成功的生育专家,经她和她的团队之手,上千粒游动的“小蝌蚪”茁壮成长为俊男靓女。
维系老年生活的社会关系中,职业生涯的延后效应带给老人的欢乐毕竟有限,失去社会关系后,老人极易产生孤独。
美国心理学教授霍华德·弗里德曼和莱斯利·马丁经20年研究发现,影响寿命的决定性因素中,人际关系位列第一。
人是群体性动物,习惯生活在群体中。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大致有:血缘(亲人)、地缘(老乡)、学缘(同学)、业缘(同事)。退休后,人际关系萎缩,而此时子女正当盛年,没时间陪父母,孤独就成为退休老人的常态,失去了人际关系,老人精神会很快枯萎,寿命也就缩短了。
随园的活力在于为老人搭建起新的人际关系平台:在血缘、地缘、学缘、业缘之后为老人建立起新的人际关系——夕缘。夕缘填补了老人退休后二三十年空窗期,这是老人特别需要的一种新型社会关系,而夕缘最大的好处是能为老年解除孤独与寂寞。
“少年宫”是老人们结交夕缘的好平台。
除了唱歌,“少年宫”另一重要活动是话聊(疗)——用聊天治愈孤独。每天晚饭后,他们聚集在食堂海阔天空地神聊,这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话聊实质上是一种深度交流,大家真诚相待,推心置腹,聊的话题极少家长里短,而是国际风云,家国兴衰,民间疾苦,“聊深藏心中的风雨人生,聊五花八门的中国故事,聊《黄帝内经》和奇门遁甲,聊欧盟各国对待难民潮的不同态度,聊无人驾驶技术在雄安落地的最新进展,聊着聊着,大家的心就渐渐靠近,聊出了真诚,聊出了信任,聊出了友谊,聊得陌生人成了风雨携手的朋友。”汪浙成说。
唱歌使人愉悦,聊天加深感情,“少年宫”成为一个温暖的家,他们共享友情和欢乐。
“我们还经常共享美食,宫主常拿水果招待大家,我夫人老家常寄福建特产,我们也拿出来一起共享;老省长与大家分享的食物最多,他喜欢红烧肉,常到省府机关食堂买几十份分送大家。”老罗笑着说。
“少年宫”成员每次回老家,都会带食物给大家共享。老省长认为,各人从老家带回的特产寄托着乡情友情,既给大家带来享受,也带有浓浓的乡愁,胡毓林回上海带来烤麸,汪浙成去内蒙带回奶茶,大家在一起品味分享这些特产,也在品味特产中蕴涵的文化。“少年宫”的人能凝聚在一起,这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夕缘使“少年宫”成员关系更密切,一家有事,众人帮忙。“少年宫”成员中有6位医生,有人病了,他们便会主动上门,给医给药给建议。汪浙成女儿得了白血病却不肯进医院,王竞、钱可大以医生的身份说服他女儿住进了医院,老省长几次生病都是王竞他们帮忙送医院的;楼奕林一度身体很差,到处求医却无效果,钱可大是消化科专家,对症下药,治好了她的病。
2017年,老伏爷的前列腺癌恶化,终至卧床不起。大家纷纷去探望。
“老伏爷,有我们呢!”大家安慰他,还为他唱起了《你激励了我》。
老伏爷走了,但他走得心安,走得愉悦,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并不孤独,有那么多朋友陪伴,有那么多欢乐相随,他很知足。
在养老问题上,“少年宫”友军“学前班”的邵敏非常睿智,他认为,一个人60岁退休,此后具有自理能力的时间大约还有二三十年。国人普遍认为,退休后最理想的状态是返聘,其实返聘只是延续原有的社会关系。他父亲退休后一直返聘,返聘结束不久母亲去世,生活便断崖式下降,不久就去世了。其实,退休后的阶段应是人生的黄金阶段,此时人生已卸下了社会责任和家庭重担,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没有了,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可以支配的时间,可随心所欲追求生活中美好的一切。
可是,多少老人却在这黄金时段中生活得孤独寂寞,痛苦不堪。
“我不愿重复职业生活,我要充分享受退休后的生活。”邵敏说。他选择随园看中的是这里能解除孤独。
“少年宫”只是随园20多个群团的一个缩影。以50后为主的“学前班”,因一起乘坐“量子号”邮轮出游而得名的“量子号”,有“花样女生”,拥有160多个成员的合唱队等等,每个群团都会组织各种活动,随园组织的活动很多,生日会、同学会、迎新会、中秋联欢、重阳九九节、春晚等,这些以群团或以活动为载体的新平台把老人们凝聚在一起,使他们在退休后能融入新的社会关系中,而这些社会关系会让他们远离孤独。
重建的社会关系使随园老人精神振奋,积极向上,有老人在常青树学院报了4个班;“花样女生”的“老少女”们为参加演出一天换几次衣服,涂口红,描眉抹粉,精心打扮;她们穿旗袍,打油纸伞,在樱花夹道上款款而行,哪像老人啊!养老生活因这些活动而丰富多彩。
老年生活不是人生的下坡路,还需要积极向上。
邵敏到随园不久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第一次&最后一次》,他在文章中说,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而进入养老阶段体验得更多的是最后一次,但在随园,老人却经历了许多第一次:80多岁了第一次学钢琴,第一次穿上演出服登台演出,第一次学唱歌……
一晚歌罢,老省长与汪浙成一起回公寓。
“邵敏的文章你看了吗?”老省长问。
“看了。”
“养老院不是人生的尽头啊!”老省长说。“人生每个阶段都有无限的可能,请谢军在随园小报上发起《我在随园的第一次》征文活动,你看如何?”
“好主意!”汪浙成赞同。
“老人要提振精神,不能消极,要积极养老,写诗、学画、练书法、学唱歌,一定要让大家融入群体中,保持良好的心态。”老省长说。
由谢军主持,随园小报上开展《在随园的第一次偶遇》征文活动得到热烈响应,老人用散文、诗歌等形式表达对积极养老的感想。
老省长还呼吁大家把人生的宝贵经验记录下来留给社会。他身体力行,把话聊时讲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2020年底出了一本《茶余饭后话旧事》,很受欢迎。
“随园老人都生活得有滋有味。生命的意义不仅是长度,更重要的是宽度与质量。”邵敏说。
夕缘为老人重建起新的人际关系,丰富多彩的活动使他们摆脱孤独,精神充实,夕缘就像一抹瑰丽的晚霞使他们的晚年生活变得斑斓多姿。
“我的人生已进入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阶段!”老汪头脸上洋溢着极度的满足感,“没想到90多岁了还能结交这么多新朋友,没想到随园的养老生活会过得这么快乐,我再也不会离开随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