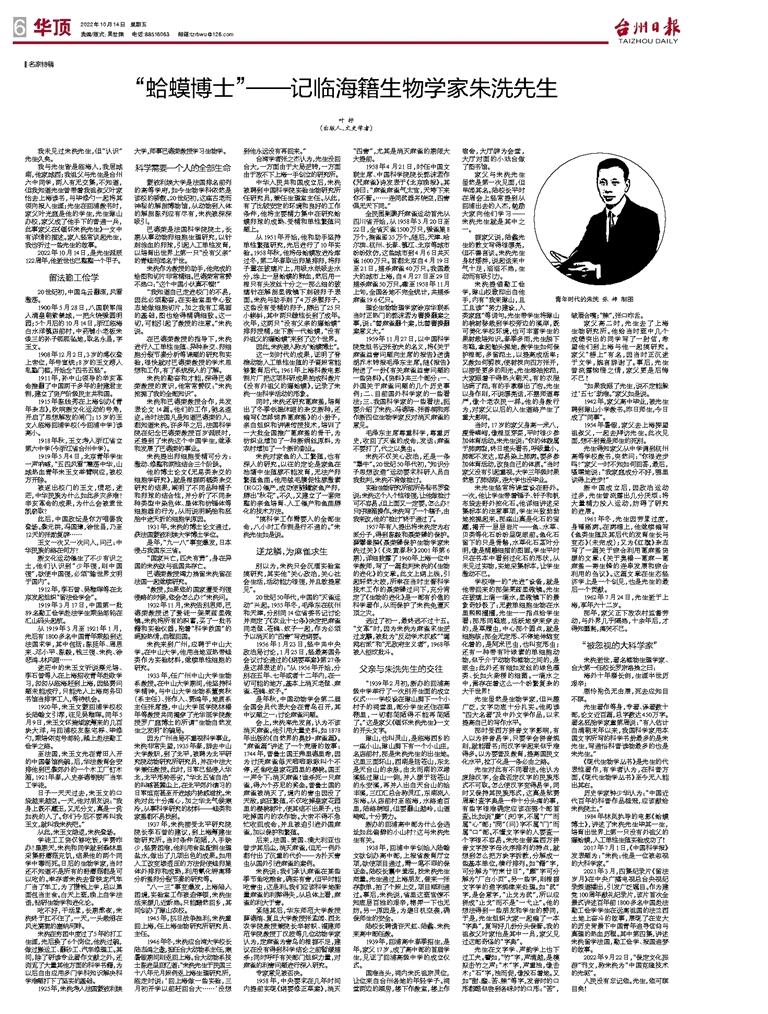我未见过朱洗先生,但“认识”先生久矣。
我与先生皆是临海人,我居城南,他家城西;我祖父与先生是台州六中同学,两人有无交集,不知道,但我知道先生曾带着我祖叔父叶家怡去上海读书,与毕修勺一起将其领向报人生涯;先生在回浦教书时,家父叶光庭是他的学生,先生琳山办校,家父成了他手下的普通一兵,此事家父在《缅怀朱洗先生》一文中有详情的描述。家人经常谈起先生,我也听过一些先生的故事。
2022年10月14日,是先生诞辰122周年,他逝世也已整整一个甲子。
留法勤工俭学
20世纪初,中国乌云翻滚,风雷激荡。
1900年5月28日,八国联军闯入清皇朝紫禁城,一把火烧毁圆明园;5个月后的10月14日,浙江临海白水洋镇店前村,中药铺小老板朱俊三的孙子呱呱坠地,取名永昌,字玉文。
1908年12月2日,3岁的溥仪登上帝位,年号宣统;8岁的玉文跨入私塾门槛,开始念“四书五经”。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15岁的玉文入临海回浦学校(今回浦中学)读高小。
1918年秋,玉文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今浙江省台州中学)。
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一声呐喊,“五四风雷”震荡中华,山城热血青年朱玉文举臂响应,被校方开除。
被逐出校门的玉文,愤怒,迷茫,中华民族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辛亥革命的成果,为什么会被袁世凯窃取?
此后,中国政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乃至12天的张勋复辟……
玉文一次又一次问人,问己:中华民族的路在何方?
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不少有识之士,他们认识到“少年强,则中国强”,欲使中国强,必须“输世界文明于国内”。
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
1919年3月17日,中国第一批89名勤工俭学赴法学生乘坐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
从1919年3月至1921年1月,先后有1800多名中国青年乘船到达法国求学,其中包括:陈延年、周恩来、邓小平、陈毅,钱三强、朱洗、徐悲鸿、林风眠……
迷茫中的朱玉文听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上海招收青年赴欧学习,匆匆从临海赶到上海,因经费问题未能成行,只能先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排字工人,等待机会。
1920年,朱玉文蒙回浦学校校长陆翰文引荐,往见吴稚晖。同年5月9日,朱玉文怀揣倾家筹来的几百块大洋,与回浦校友陈宅桴、毕修勺,乘培依克号邮轮,踏上赴法勤工俭学之路。
至法国,朱玉文先在青田人开的中国餐馆洗碗,后,华法教育会安排他到巴黎郊外的一个木工厂钉木箱,1921年春,入史奈德钢铁厂当车工学徒。
日子一天天过去,朱玉文的口袋越来越空。一天,他对朋友说:“我身上既不藏玉,又无分文,真是一贫如洗的人了。你们今后不要再叫我玉文,就叫我朱洗吧。”
从此,朱玉文隐退,朱洗登场。
学徒工工资仅够吃饭,学费咋办?星期天,朱洗和同学就到森林里采集野蘑菇充饥,结果他的两个同学中毒而死。日后的生物学家,当时还不知道不是所有的野蘑菇都是可以吃的。幸存者朱洗去雪铁龙汽车厂当了车工,为了攒钱上学,总以黑面包当主食。白天上班,晚上自学法语,钻研生物学和进化论。
吃不好,干活累,长期熬夜,朱洗终于扛不住了,一天,一头栽倒在风光旖旎的塞纳河畔。
朱洗在穷困中度过了5年的打工生涯,先后换了6个岗位,他洗过碗,做过搬运工、翻砂工、汽车修理工。其间,除了研读专业著作文献之外,还浏览了大量其他方面的科学书籍,为以后自由应用多门学科知识解决科学难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朱洗考入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师事巴德荣教授学习生物学。
科学需要一个人的全部生命
蒙彼利埃大学是法国排名前列的高等学府,如今生物学科依然是该校的骄傲。20世纪初,这座古老而神秘的解剖博物馆,从动物到人体的解剖陈列应有尽有,朱洗被深深吸引。
巴德荣是法国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动物卵细胞生理研究,以针刺涂血的卵球,引起人工单性发育,以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没有父亲”的青蛙而闻名于世。
朱洗作为教授的助手,他完成的绘图和切片非常精细。巴德荣常常赞不绝口:“这个中国小伙真不错!”
“我知道自己走进校门的不易,因此必须勤奋,在实验室里专心致志地做细胞切片,加之我有工笔画的基础,图也绘得精确细致。这一切,可能引起了教授的注意。”朱洗说。
在巴德荣教授的指导下,朱洗进行人工单性生殖、异种杂交、卵细胞分裂节奏分析等课题的研究和实验,很快就对巴德荣教授的学术思想和工作,有了系统深入的了解。
朱洗的勤奋和才能,深得巴德荣教授的赏识,他常常赞叹:“朱洗挖掘了我的全部知识”。
朱洗和巴德荣教授合作,共发表论文14篇。他们的工作,驰名遐迩。当时法国凡是知道巴德荣的人,都知道朱洗。许多年之后,法国科学院在纪念巴德荣教授百岁诞辰时,还提到了朱洗这个中国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巴德荣的事业。
朱洗提出卵细胞受精可分为:激动、修整和两性结合三个阶段。
他的博士论文《无尾类杂交的细胞学研究》,就是根据两栖类杂交研究的结果,阐明了不同品种精子和卵球的结合性,并分析了不同杂种类型中染色体、星体和纺锤体等细胞器的行为,从而说明畸胎和胚胎中途夭折的细胞学原因。
1931年,朱洗的博士论文通过,获法国蒙彼利埃大学博士学位。
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在异国的朱洗欲与祖国共存亡。
巴德荣教授竭力挽留朱洗留在法国一起继续研究。
“教授,如果您的国家遭受列强侵略的时候,您会怎么办?”朱洗问。
1932年11月,朱洗告别恩师,巴德荣教授送了爱徒一架莱兹显微镜。朱洗将所有的积蓄,买了一批书籍和实验仪器,抱着“科学救国”的满腔热情,启程回国。
朱洗来到广州,应聘于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他用当地亚热带蛙类作为实验材料,继续单性细胞的研究。
1933年,任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在中山大学期间,他坚持科学精神,与中山大学生物系董爽秋(系主任)、张作人、费鸿年,地质系主任张席提,中山大学医学院林椿年等教授共同揭穿了光华医学院教授罗广庭博士的所谓“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的骗局。
因为广州当局不重视科学事业,朱洗非常失望,1935年春,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到了北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并在中法大学兼任教授。此时,日军已经侵入华北,北平形势恶劣,“华北五省自治”的叫喊甚嚣尘上,在北平郊外演习的日军坦克甚至开进城内扬威滋扰。朱洗对此十分痛心,加之华北气候寒冷,从事科学研究的材料——蛙类和家蚕都不易找到。
1937年,朱洗接受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的建议,到上海筹建生物研究所。当时条件简陋,人手缺少,经费困难,他利用食盐配制生理盐水,做出了几项出色的成果。如用人工改变渗透压的方法促使蛙卵巢体外排卵和成熟,利用氰化钾离释分析蚕卵分裂节奏的研究等。
“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陷入困境,实验室工作被迫停顿,朱洗生活来源几近断绝。只能黯然回乡,其间创办了琳山农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朱洗重回上海,任上海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主任。
1946年冬,朱洗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邀,担任台大动物系主任,寒暑假期间则返回上海。台大动物系技士陈进呈回忆道:“朱洗先生于民国三十八年元月照例返上海生理研究所,临走时说:‘回上海做一些实验,三月初开学以前赶回台大……’没想到他永远没有再回来。”
台湾学者张之杰认为,先生没回台大,一方面由于大局逆转,一方面由于放不下上海一手创立的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洗被聘到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任生理室主任。从此,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和良好的工作条件,他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蛤蟆卵球的成熟、受精和单性繁殖问题上。
从1951年开始,他和助手坚持单性繁殖研究,先后进行了10年实验。1958年秋,他将母蛤蟆放进冷库过冬,第二年春取出卵巢排卵,将卵子置在玻璃片上,用吸水纸吸去水分,涂上一层蛤蟆的鲜血,然后用一根只有头发丝十分之一那么细的玻璃针在解剖显微镜下刺破卵子表面。朱洗与助手刺了4万多颗卵子,这些没有受精的卵子,孵出了25只小蝌蚪,其中两只雌性长到了成年。次年,这两只“没有父亲的癞蛤蟆”排卵授精,生下新一代蛤蟆,“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来到了这个世界。
因此,朱洗被人称为“蛤蟆博士”。
这一划时代的成果,证明了脊椎动物人工单性生殖的子裔照常能够繁育后代。1961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把这项科研成果拍成科教片《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记录了朱洗一生科学活动的形象。
同时,朱洗还研究蓖麻蚕,培育出了冬季低温休眠的杂交新种,还编写《怎样饲养蓖麻蚕》的小册子,亲自组织和讲课传授技术,培训了一大批全国推广蓖麻蚕的骨干,为纺织业增加了一种新绢丝原料,为农村增加了一个新的副业。
朱洗对家鱼的人工繁殖,也有深入的研究。以往的定论是家鱼在池塘中生殖腺不能发育,无法产卵繁殖鱼苗。他用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催产,成功使鲢鳙家鱼产卵,孵出“秋花”。不久,又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亲鱼培育、人工催产和鱼苗孵化的技术方法。
“搞科学工作需要人的全部生命,八小时工作制是行不通的。”朱洗先生如是说。
逆龙鳞,为麻雀求生
别以为,朱洗只会沉湎实验室搞研究,其实他“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生活,活动能力很强,并且敢提意见”。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灭雀运动”兴起。1955年冬,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省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决定把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作为必须予以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1956年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是这样表述的:“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是年秋,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青岛召开,其中议题之一:讨论麻雀问题。
会上,朱洗率先发言,认为不该消灭麻雀。他引用大量史料,如1878年出版的《自然界的奥妙·麻雀篇》。“麻雀篇”讲述了一个荒唐的故事: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还偷吃皇家花园里的樱桃。国王一声令下:消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得六个芬尼的奖金。普鲁士国的麻雀被消灭了,境内的害虫因没了天敌,疯狂繁殖,不仅吃掉皇家花园里的樱桃树叶,使其结不出果子,也吃掉国内的农作物。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引进外国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
后来,法国、美国、澳大利亚也曾步其后尘,消灭麻雀,但无一例外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案例。
朱洗说:我们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偷吃粮食,确实有害,但平时能吃害虫,这是利。我们应该科学地衡量麻雀的利弊得失,从总体上看,麻雀的利大于害。
紧随其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利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专家意见被否决。
1958年,中央要求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纲要修正草案》,消灭“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的期限大大提前。
1958年4月21日,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咒麻雀》诗发表于《北京晚报》。其诗曰:“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首先从四川省开始,从1958年3月20日至22日,全省灭雀1500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随后,天津、哈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纷纷效仿,这些城市到4月6日共灭雀1600万只。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杀麻雀40万只。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自4月27日至29日捕杀麻雀50万只。截至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统计,共捕杀麻雀19.6亿只。
理论生物物理学家徐京华联系当时正热门的郭沫若为曹操翻案之事,说:“替麻雀翻个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
1959年11月27日,以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主席。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扼要介绍了朱洗、冯德培、张香桐和郑作新四位生物学家反对消灭麻雀的意见。
毛泽东主席尊重科学,尊重历史,收回了灭雀的成命,发话: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朱洗不仅关心政治,还是一条“犟牛”。20世纪50年代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科研人员自我批判,朱洗不肯做检讨。
实验生物研究所前所务秘书罗登说:朱洗这个人个性很强,让他做检讨可不容易。但上面又一定要,怎么办?只好暗箱操作。朱洗写了一个稿子,由我来改,他的“检讨”终于通过了。
1957年有人提出将朱洗定为右派分子,得到陈毅和聂荣臻的保护。薛攀皋撰《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详细披露了1960年上海一位中学教师,写了一篇批判朱洗的《生物的进化》的文章。此文上纲上线,引起轩然大波,所幸在当时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过问下,充分肯定了《生物的进化》是一部有价值的科学著作,从而保护了朱洗免遭灭顶之灾。
逃过了初一,最终逃不过十五。“文革”时,因为朱洗为麻雀求生逆过龙麟,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和“无政府主义者”,1968年被人刨坟批斗。
父亲与朱洗先生的交往
“1939年2月初,新办的回浦高级中学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成立仪式……学校设在琳山脚下一个小村子的祠堂里,部分学生还住在草棚里,一切都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这是家父《缅怀朱洗先生》一文的开头文字。
琳山,也叫灵山,是临海西乡的一座小山。琳山脚下有一个小山庄,名店前村,那是朱洗先生的出生地。这里三面环山,西南是括苍山,东北是天台山的余脉,由北而南的双港溪经过琳山一侧,并入源于括苍山的永安溪,再并入出自天台山的始丰溪,三江汇总合称灵江,东南流入东海。从店前村至临海,水路逾百里,陆路稍短,但要翻山越岭,山道崎岖,十分费力。
新办的回浦高中部为什么会选址如此偏僻的小山村?这与朱洗先生有关。
1938年,回浦中学创始人陆翰文欲创办高中部,上报省教育厅立项,欲使项目通过,需一笔不菲的保证金。陆校长囊中羞涩,找朱洗先生商量。先生通过上海朋友,借来一张存款单,拍了个照上交,项目顺利通过。事后,朱洗说,省里这班官僚不知底层百姓的艰辛,糊弄一下也无妨。另一原因是,为避日机空袭,确保师生的安全。
陆校长聘请许天虹、陆蠡、朱洗来高中部任教。
1939年,回浦高中春季招生,是年,家父17岁,成了高中部的首届学生,见证了回浦高级中学的成立仪式。
国难当头,祠内朱氏祖宗灵位,让位来自台州各地的年轻学子。祠堂两边的厢房,楼下作教室,楼上作宿舍,大厅辟为会堂,大厅对面的小戏台做了图书馆。
家父与朱洗先生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早闻其名。陆校长平时在周会上经常提到从回浦出去的人杰,勉励大家向他们学习——朱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据家父说,陆蠡先生的散文写得很漂亮,但不善言谈。朱洗先生身材矮胖,说起话来中气十足,滔滔不绝,生动而有吸引力。
朱洗提倡勤工俭学,琳山校歌即出自他手,内有“我来琳山,且工且读”“努力建设,人类家庭”等词句。先生带学生将琳山的桃树移栽到学校旁边的溪岸,既可美化学校环境,也可丰富学生的果树栽培知识。春季多雨,先生脱下布鞋,拿起锄头掘地,教学生如何保护根部,多留泥土,以提高成活率;又教如何剪枝,使树枝向四方张开,以接受更多的阳光。先生卷袖挖泥,大家跟着干得热火朝天。有的衣服沾满了泥,有的手掌磨出了泡。先生以身作则,不说漂亮话,不摆师道尊严,像个老农民一样。他的身教行为,对家父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时,17岁的家父身高一米八,瘦骨嶙峋,像根豆芽菜,平时很少参加体育活动。朱先生说:“你的体貌属于肺病型,终日埋头看书,呼吸量小,肺部不发达,容易染上肺病。要多参加体育活动,改良自己的体质。”当时家父没有引起重视,大学三年级时果然患了肺结核,连大学也没毕业。
朱先生经常将课堂设在野外。一次,他让学生带着锤子、钎子和帆布袋去野外挖化石。他详细讲述采集标本的注意事项,学生兴致勃勃地挖掘起来。那座山真是化石的宝藏,揭开一层层岩片——鱼、水草、贝类等化石纷纷呈现眼前。鱼化石留下的只是骨骼,水草化石茎叶分明,像是精雕细描的图画。学生平时只在书本中看到过化石的形状,从未见过实物,实地采集标本,让学生激动不已。
学校唯一的“先进”设备,就是他带回来的那架莱兹显微镜。先生在玻璃上滴一滴水,显微镜下的景象奇妙极了:无数单细胞生物在水里熙熙攘攘,先生一一指点给学生看:那形同鞋底,活跃地穿来穿去的,是草履虫,中心那个圆点,就是细胞核;那全无定形、不停地伸缩变化着的,是阿米巴虫,也叫变形虫;还有一种带有叶绿素的单细胞动物,似乎介于动物和植物之间的,是眼虫;此外还有细如发丝的绿色藻类、长如火柴梗的细菌。一滴水之中,竟存在着这么一个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
先生虽然是生物学家,但兴趣广泛,文字功底十分扎实。他阅读“四大名著”及中外文学作品,以求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那时受西方拼音文字影响,有人以为拼音易学,只要学会拼音规则,就能看书;而汉字学起来似乎难得多。以为要普及教育,提高国民文化水平,拉丁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废除汉字,全盘否定汉字的民族形式不可取。怎么使汉字变得易学,同时又保持其民族形式,这真是煞费周章!查字典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有些字很难确定应该在哪个部首查。比如说“慶”(庆)字,不属“广”而属“心”部;“問”(问)字不属“门”而属“口”部。不懂文字学的人要查一个字很不容易。朱先生借鉴西方拼音文字按字母次序排列的特点,就想到怎么把方块字拆散,分解成一些基本单位,横行排列。如“籍”字,可分解为“竹耒廿日”,“願”字可分解为“厂白小页”。另一些字,则根据文字学的造字规律来处理。如“武”字,是会意字,“止戈为武”,所以应拼成“止戈”而不是“一弋止”。他的想法得到一些朋友和学生的赞同,于是,先生组织大家一起编了一本“字典”,复写好几份分头保管。我的祖叔父叶家怡是其中一员,家父见过这部奇怪的“字典”。
先生在文字学、声韵学上也下过工夫。譬如,“竹”字,声清越,是模拟击竹之声;“木”字,声重浊,像击木;“石”字,浊而促,像投石着地。又如“甜、酸、苦、辣”等字,发音时的口形都酷似尝到各味时的口形:“苦”,皱眉合嘴;“辣”,张口咋舌。
家父高二时,先生去了上海生物研究所。他给当时班中几个成绩突出的同学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们到上海与他一起搞研究。家父“榜上”有名,因当时正沉迷于文学,婉言辞谢了。事后,先生曾流露惋惜之情,家父更是后悔不已!
“如果我跟了先生,说不定能躲过‘五七’劫难。”家父如是说。
1942年,家父高中毕业,被先生聘到琳山小学教书。昨日师生,今日成了“同事”。
1954年暑假,家父去上海探望祖叔父,一起去拜访先生。此次见面,想不到竟是师生的死别。
先生得知家父从中学调到杭州高等学校教书,突然问:“你很进步吗?”家父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最后,嗫嚅地说:“我家庭成分不好,哪里谈得上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因政治运动过多,先生曾流露出几分厌烦:将大量精力投入运动,妨碍了研究的进展。
1961年冬,先生因劳累过度,身罹癌病。在病榻上,他继续编写《鱼类生殖及其后代的发育生长与变态》(未完成);又为《红旗》杂志写了一篇关于综合利用蓖麻蚕资源的文章:《关于臭椿—蓖麻—蓖麻蚕—寄生蜂的连串发展和综合利用的刍议》。这篇文章在生态经济学上是一个创见,也是先生的最后一个贡献。
1962年7月24日,先生逝于上海,享年六十二岁。
那年,家父正下放农村监督劳动,与外界几乎隔绝,十余年后,才得知噩耗,痛哭不已。
“被忽视的大科学家”
朱洗逝世,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台大第一任校长罗宗洛挽之曰:
海外十年磨长剑,生涯半世历艰辛;
剧怜抱负无由展,死去应知目不瞑。
先生著作等身,专著、译著数十部,论文近百篇,总字数达450万字。著名胚胎学家童第周说:“有人估计自清朝末年以来,我国科学家用本国文字所写的科学书册最多的是朱先生,写通俗科普读物最多的也是朱先生。”
《现代生物学丛书》是先生的代表性著作,有学者认为,在科普方面,《现代生物学丛书》至今无人能出其右。
历史学家钟少华认为:“中国近代百年的科普作品桂冠,应该献给朱洗院士。”
1984年林岚执导的电影《蛤蟆博士》,讲述了朱洗先生毕其一生,培育出世界上第一只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人工单性生殖实验成功了!
2017年7月1日,《中国科学报》发表题为:“朱洗:他是一位被忽视的大科学家。”
2021年3月,四集纪录片《留法岁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引发广泛瞩目。作为建党100周年献礼纪录片,该片首次全景式讲述百年前1800多名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在远离祖国的法兰西土地上奋斗的故事,展现了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青年追寻信仰与真理的热血历程。其中第四集,讲述朱洗留学法国,勤工俭学、报国追梦的故事。
2022年9月22日,“保定文化旅游”刊文,称朱洗为“中国克隆技术的先驱”。
人民没有忘记您。先生,您可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