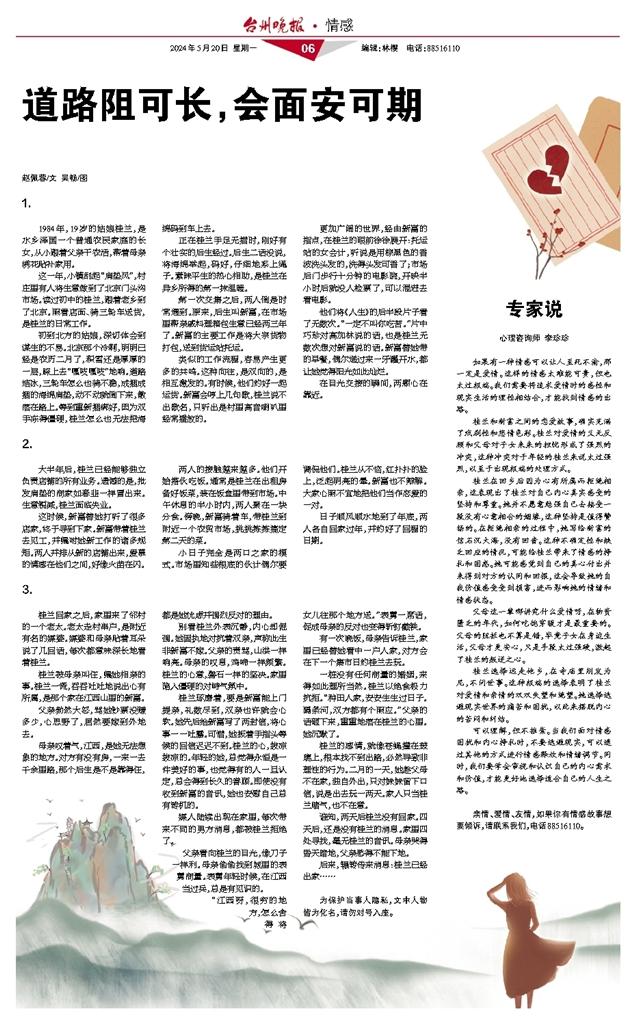赵佩蓉/文 吴畅/图
1.
1984年,19岁的姑娘桂兰,是水乡泽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长女,从小跟着父亲干农活,帮着母亲绣花贴补家用。
这一年,小镇刮起“肩垫风”,村庄里有人将生意做到了北京门头沟市场。读过初中的桂兰,跟着老乡到了北京。照看店面、骑三轮车送货,是桂兰的日常工作。
初到北方的姑娘,深切体会到谋生的不易。北京那个冷啊,明明已经是农历二月了,积雪还是厚厚的一层,踩上去“嘎吱嘎吱”地响。道路结冰,三轮车怎么也骑不稳,成捆成捆的海绵肩垫,动不动就倒下来,散落在路上。等到重新捆绑好,因为双手冻得僵硬,桂兰怎么也无法把海绵码到车上去。
正在桂兰手足无措时,刚好有个壮实的后生经过。后生二话没说,将海绵举起,码好,仔细地系上绳子。素昧平生的热心相助,是桂兰在异乡所得的第一抹温暖。
第一次交集之后,两人倒是时常遇到。原来,后生叫新富,在市场里帮亲戚料理箱包生意已经两三年了。新富的主要工作是将大宗货物打包,送到货运站托运。
类似的工作流程,容易产生更多的共鸣。这种向往,是双向的,是相互激发的。有时候,他们约好一起运货。新富会哼上几句歌,桂兰说不出歌名,只听出是村里高音喇叭里经常播放的。
更加广阔的世界,经由新富的指点,在桂兰的眼前徐徐展开:托运站的女会计,听说是用棕黑色的香波洗头发的,洗得头发可香了;市场后门步行十分钟的电影院,开映半小时后就没人检票了,可以混进去看电影。
他们将《人生》的后半段片子看了无数次。“一定不叫你吃苦。”片中巧珍对高加林说的话,也是桂兰无数次想对新富说的话。新富替她带的早餐,偶尔递过来一牙罐开水,都让她觉得阳光如此灿烂。
在目光交接的瞬间,两颗心在靠近。
2.
大半年后,桂兰已经能够独立负责店铺的所有业务。遗憾的是,批发肩垫的商家如春韭一样冒出来。生意锐减,桂兰面临失业。
这时候,新富替她打听了很多店家,终于寻到下家。新富带着桂兰去见工,并嘱咐她新工作的诸多规矩。两人并排从新的店铺出来,爱慕的情感在他们之间,好像火苗在闪。
两人的接触越来越多。他们开始搭伙吃饭。通常是桂兰在出租房备好饭菜,装在饭盒里带到市场。中午休息的半小时内,两人聚在一块分食。傍晚,新富骑着车,带桂兰到附近一个农贸市场,挑挑拣拣搞定第二天的菜。
小日子完全是两口之家的模式。市场里知些根底的伙计偶尔要调侃他们。桂兰从不恼,红扑扑的脸上,泛起明亮的晕。新富也不辩解。大家心照不宜地把他们当作恋爱的一对。
日子顺风顺水地到了年底,两人各自回家过年,并约好了回程的日期。
3.
桂兰回家之后,家里来了邻村的一个老太。老太走村串户,是附近有名的媒婆。媒婆和母亲贴着耳朵说了几回话,每次都意味深长地看着桂兰。
桂兰被母亲叫住,嘱她相亲的事。桂兰一慌,吞吞吐吐地说出心有所属,是那个家在江西山里的新富。
父亲勃然大怒,骂她钞票没赚多少,心思野了,居然要嫁到外地去。
母亲叹着气,江西,是她无法想象的地方。对方有没有房,一来一去千余里路,那个后生是不是靠得住,都是她忧虑并强烈反对的理由。
别看桂兰外表沉静,内心却倔强。她固执地对抗着双亲,声称此生非新富不嫁。父亲的责骂,山洪一样响亮。母亲的叹息,鸡啼一样频繁。桂兰的心意,磐石一样的坚决。家里陷入僵硬的对峙气氛中。
桂兰琢磨着,要是新富能上门提亲,礼数尽到,双亲也许就会心软。她先后给新富写了两封信,将心事一一吐露。可惜,她扳着手指头等候的回信迟迟不到。桂兰的心,拔凉拔凉的。年轻的她,总觉得永恒是一件美好的事,也觉得有的人一旦认定,总会得到长久的眷顾。即使没有收到新富的音讯,她也安慰自己总有转机的。
媒人陆续出现在家里,每次带来不同的男方消息,都被桂兰拒绝了。
父亲看向桂兰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利。母亲偷偷找到城里的表舅商量。表舅年轻时候,在江西当过兵,总是有见识的。
“江西呀,很穷的地方,怎么舍得将女儿往那个地方送。”表舅一席话,促成母亲的反对也变得斩钉截铁。
有一次晚饭,母亲告诉桂兰,家里已经替她看中一户人家,对方会在下一个集市日约桂兰去玩。
一桩没有任何商量的婚姻,来得如此理所当然。桂兰以绝食极力抗拒。“种田人家,安安生生过日子。隔条河,双方都有个照应。”父亲的话砸下来,重重地落在桂兰的心里。她沉默了。
桂兰的感情,就像苍蝇撞在玻璃上,根本找不到出路,必然导致非理性的行为。二月的一天,她趁父母不在家,独自外出,只对妹妹留下口信,说是出去玩一两天。家人只当桂兰赌气,也不在意。
谁知,两天后桂兰没有回家。四天后,还是没有桂兰的消息。家里四处寻找,毫无桂兰的音讯。母亲哭得昏天暗地,父亲愁得不能下地。
后来,辗转传来消息:桂兰已经出家……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人物皆为化名,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