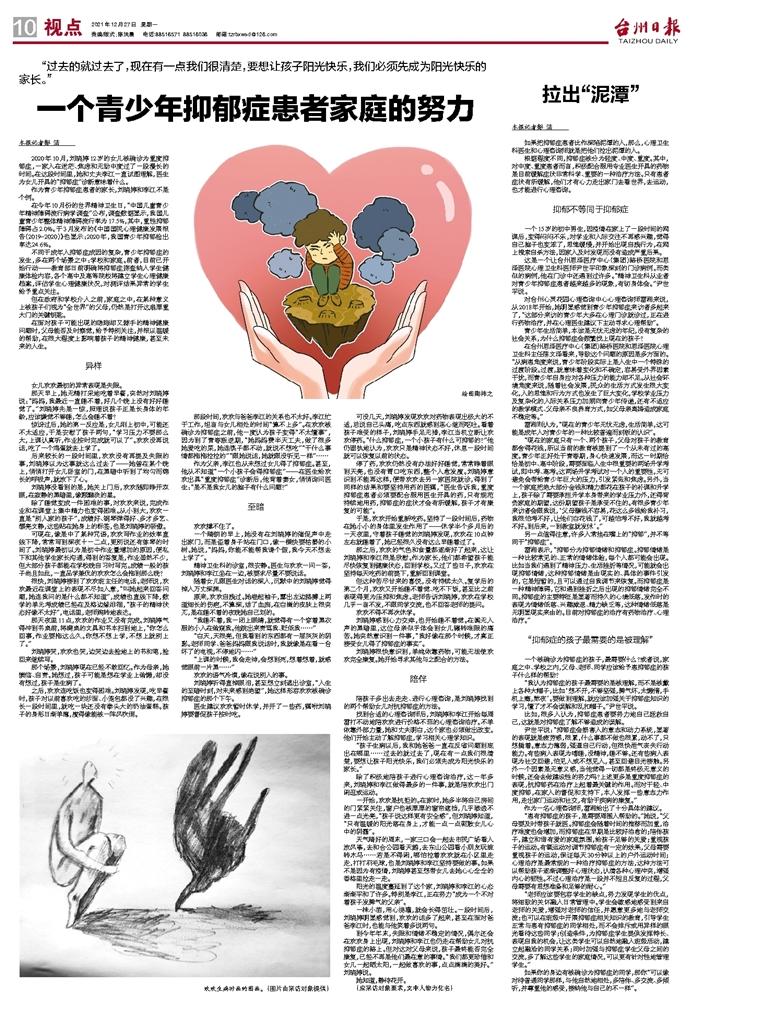本报记者彭 洁
2020年10月,刘晓婷12岁的女儿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一家人在迷茫、焦虑和无助中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和丈夫李江一直试图理解,医生为女儿开具的“抑郁症”诊断意味着什么。
作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家长,刘晓婷和李江不是个例。
在今年10月份的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公布,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其中,重性抑郁障碍占2.0%。于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也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达24.6%。
不同于成年人抑郁症成因的复杂,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多在两个场景之中:学校和家庭。前者,目前已开始行动——教育部日前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但在政府和学校介入之前,家庭之中,在某种意义上被孩子们视为“全世界”的父母,仍然是打开这扇厚重大门的关键钥匙。
在面对孩子可能出现的隐晦却又棘手的精神健康问题时,父母能否及时察觉,给予特别关注,并报以温暖的帮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精神健康,甚至未来的人生。
异样
女儿欢欢最初的异常表现是失眠。
那天早上,她无精打采地吃着早餐,突然对刘晓婷说:“妈妈,我最近一直睡不着,好几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刘晓婷先是一惊,照理说孩子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应该嫌觉不够睡,怎么会睡不着?
惊讶过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女儿刚上初中,可能还不太适应,于是安慰了孩子两句,“学习压力不要那么大,上课认真听,作业按时完成就可以了”。欢欢没再说话,吃了一个鸡蛋就去上学了。
后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欢欢没有再提及失眠的事,刘晓婷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她曾在某个晚上,悄悄打开女儿卧室的门,在黑暗中听到了均匀而绵长的呼吸声,就放下了心。
刘晓婷没看到的是,她关上门后,欢欢随即睁开双眼,在寂静的黑暗里,像颗黯淡的星。
除了睡觉变成一件困难的事,对欢欢来说,完成作业和在课堂上集中精力也变得困难。从小到大,欢欢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好、钢琴弹得好、多才多艺、漂亮文静,这些贴在她身上的标签,也是刘晓婷的骄傲。
可现在,像是中了某种咒语,欢欢写作业的效率直线下降,常常写到深夜十一二点,更别说还有练琴的时间了。刘晓婷最初以为是初中作业量增加的原因,便私下和其他学生家长沟通,得到的答复是,作业虽然不少,但大部分孩子都能在学校晚自习时写完。成绩一般的孩子尚且如此,一直品学兼优的欢欢怎么会拖到那么晚?
很快,刘晓婷接到了欢欢班主任的电话。老师说,欢欢最近在课堂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叫她起来回答问题,她连我问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成绩也直线下降,数学的单元考成绩已经在及格边缘徘徊,“孩子的精神状态好像不太好”,电话里,老师婉转地表达。
那天夜里11点,欢欢的作业又没有完成。刘晓婷气得冲到书桌前,将满桌的文具和书本扫到地上,“你怎么回事,作业要拖这么久。你想不想上学,不想上就别上了。”
刘晓婷哭,欢欢也哭,边哭边去捡地上的书和笔,捡回来继续写。
那个场景,刘晓婷现在已经不敢回忆。作为母亲,她懊恼、自责。她想过,孩子可能是想在学业上偷懒,却没有想过,孩子是生病了。
之后,欢欢连吃饭也变得困难。刘晓婷发现,吃早餐时,孩子对以前喜欢吃的炒面、小笼包都没了兴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吃一块还没有拳头大的奶油蛋糕。孩子的身形日渐单薄,瘦得像能被一阵风吹倒。
那段时间,欢欢与爸爸李江的关系也不太好。李江忙于工作,坦言与女儿相处的时间“算不上多”。在欢欢被确诊为抑郁症之前,他一度认为孩子变得“不太懂事”,因为到了青春叛逆期,“她妈妈费半天工夫,做了很多她爱吃的菜,她连筷子都不动,就说不想吃”“干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的”“跟她说话,她就跟没听见一样”……
作为父亲,李江也从未想过女儿得了抑郁症。甚至,他从不知道“一个小孩子会得抑郁症”——在医生给欢欢出具“重度抑郁症”诊断后,他背着妻女,悄悄询问医生:“是不是我女儿的脑子有什么问题?”
至暗
欢欢撑不住了。
一个晴朗的早上,她没有在刘晓婷的催促声中走出家门,而是歪着身子站在门口,像一棵快要枯萎的小树。她说,“妈妈,你能不能帮我请个假,我今天不想去上学了”。
精神卫生科的诊室,很安静。医生与欢欢一问一答,刘晓婷和李江坐在一边,被要求尽量不要说话。
随着女儿跟医生对话的深入,沉默中的刘晓婷觉得掉入万丈深渊。
原来,欢欢自残过。她卷起袖子,露出左边胳膊上两道细长的伤疤,不算深,结了血痂,在白嫩的皮肤上很突兀,是在睡不着的夜晚她自己划的。
“我睡不着,我一闭上眼睛,就觉得有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小人在偷窥我。他跳出来责骂我、贬低我……”
“白天,天很亮,但我看到的东西都有一层灰灰的阴影。老师同学、爸爸妈妈跟我说话时,我就像是在看一台坏了的电视,不停地闪……”
“上课的时候,我会走神,会想到死,想着想着,就感觉眼前一片黑……”
欢欢的语气冷漠,像在说别人的事。
刘晓婷听得直掉眼泪,甚至想立刻逃出诊室,“人生的至暗时刻,对未来感到绝望”,她这样形容欢欢被确诊抑郁症的那个下午。
医生建议欢欢暂时休学,并开了一些药,嘱咐刘晓婷要督促孩子按时吃。
可没几天,刘晓婷发现欢欢对药物表现出极大的不适,总说自己头痛,吃点东西就感到恶心继而呕吐。看着孩子难受的样子,刘晓婷手足无措,李江当机立断让欢欢停药。“什么抑郁症,一个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他仍固执地认为,欢欢只是精神状态不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恢复以前的状态。
停了药,欢欢仍然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常常睁着眼到天亮,也没有胃口吃东西,整个人愈发瘦。刘晓婷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便带欢欢去另一家医院就诊,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和要坚持用药的医嘱,“医生告诉我,重度抑郁症患者必须要配合服用医生开具的药,只有规范持续地用药,抑郁症的症状才会有所缓解,孩子才有康复的可能”。
于是,欢欢开始重新吃药。坚持了一段时间后,药物在她小小的身体里发生作用了——休学半个多月后的一天夜里,守着孩子睡觉的刘晓婷发现,欢欢在10点钟左右就睡着了,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早睡着过了。
那之后,欢欢的气色和食量都逐渐好了起来,这让刘晓婷和李江很是欣慰。作为家长,他们都希望孩子能尽快恢复到健康状态,回到学校。又过了些日子,欢欢在坚持每天吃药的前提下,重新回到课堂。
但这种苦尽甘来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复学后的第二个月,欢欢又开始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甚至比之前表现得更为压抑和焦虑。老师告诉刘晓婷,欢欢在学校几乎一言不发,不跟同学交流,也不回答老师的提问。
欢欢不得不再次休学。
刘晓婷感到心力交瘁,也开始睡不着觉。在阒无人声的黑暗里,这位母亲似乎体会到女儿辗转难眠的痛苦。她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我好像在那个时候,才真正接受女儿得了抑郁症的事实”。
刘晓婷很快意识到,单纯依靠药物,可能无法使欢欢完全康复。她开始寻求其他与之配合的方法。
陪伴
陪孩子多出去走走、进行心理咨询,是刘晓婷找到的两个帮助女儿对抗抑郁症的方法。
找到合适的心理咨询师后,刘晓婷和李江开始每周雷打不动地陪欢欢进行价格不菲的心理咨询治疗。不单依靠外部力量,她和丈夫明白,这个家也必须做出改变。他们开始主动了解抑郁症,学习相关心理学知识。
“孩子生病以后,我和她爸爸一直在反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过去的就过去了,现在有一点我们很清楚,要想让孩子阳光快乐,我们必须先成为阳光快乐的家长。”
除了积极地陪孩子进行心理咨询治疗,这一年多来,刘晓婷和李江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陪欢欢出门闲逛或运动。
一开始,欢欢是抗拒的。在家时,她多半将自己房间的门紧紧关住,窗户也被厚厚的窗帘遮挡,几乎渗透不进一点光亮,“孩子说这样更有安全感”,但刘晓婷知道,“只有温暖的阳光落在身上,才能一点一点驱散女儿心中的阴霾”。
天气晴好的周末,一家三口会一起去市民广场看人放风筝,去和合公园看天鹅,去东山公园看小朋友玩旋转木马……若是不得闲,哪怕拉着欢欢就在小区里走走,打打羽毛球,也是刘晓婷和李江坚持要做的事。如果不是因为有疫情,刘晓婷甚至想带女儿去她心心念念的香格里拉走一走。
阳光的温度蔓延到了这个家,刘晓婷和李江的心态渐渐平和了许多。特别是李江,正在努力“成为一个不对着孩子发脾气的父亲”。
一株小苗,用心浇灌,就会长得茁壮。一段时间后,刘晓婷明显感觉到,欢欢的话多了起来,甚至在面对爸爸李江时,也能与他笑着多说两句。
到今年年末,失眠和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偶尔还会在欢欢身上出现,刘晓婷和李江也仍走在帮助女儿对抗抑郁症的路上。但对这对父母来说,孩子最终能否完全康复,已经不再是他们最在意的事情。“我们都更珍惜和女儿一起晒太阳,一起做喜欢的事,点点滴滴的美好。”刘晓婷说。
她知道,静待花开。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