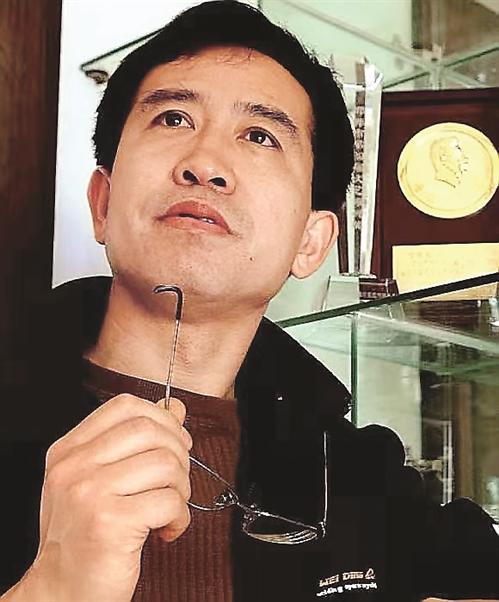编者按:民营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金名片,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民营企业家是浙江的宝贵资源和财富。
黄岩曾出台全国首个股份合作制“红头文件”,是中国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祥地之一。1979年,池幼章创办黄岩利民皮鞋厂,上世纪80年代“利民”成为浙江首批产值过亿的企业。世纪之交,“利民”濒临破产,之后几经波折转型升级,成为吉利集团核心供应商。池幼章身上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先行者风范,百折不挠的执着追求,一生利民的无私奉献,很好地诠释了新时代浙商精神。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台州“再创民营经济新辉煌”殷切嘱托20周年,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报告文学《橘香——打不败的浙商池幼章》的出版发行,将为浙江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为台州建设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市,贡献“浙商新四千”精神动能。
本报记者任 健 /文
【1】 橘花摇曳四月风,绿波丛中露玉容。正是橘花飘香的时节,我们迎来您的报告文学《橘香》的出版发行。祝贺!作为新世纪以来唯一两度获鲁迅文学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作家,您如何看待这本新书在您创作生涯中的分量?
李:分量很重。2005年,我第一次获鲁迅文学奖后,雄心勃勃,想着寻找重大题材写作。当时,以温州为代表的浙商正风行全国,于是,我便向中国作家协会递交了创作《温州商人》的计划,并得到支持。我曾3次去温州采访,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完成。这是我心中的一大遗憾,总是放不下。2019年,黄岩方面联系我,希望采写台州商人池幼章。我调查了池先生的事迹后,大为惊奇,他不仅是浙商代表,还曾是一位作家。或者可以说,他更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商人代表。而且,温州台州地缘相近、人文相通,这不刚好可以实现多年前的愿望吗?于是,欣然应允,便有了这本报告文学。池先生的创业经历,也充分展示了“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的浙商“新四千”精神。
【2】 写作此书,您投入了大量精力,采访了很多人,采访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人哪些事?
李:写作《橘香》,我在黄岩住了一周,那是去年3月下旬,橘花还未绽放,只有零星的一颗颗小米粒,香气被包裹着。那一周时间,我与池先生天天见面,在公司里深入交谈,到车间走访,与技术团队成员座谈,多次到他家中跟他的家人一起吃饭交谈。印象深刻的人很多,比如池先生的长子池宁平,他多年以来一直在父亲身边,对于父亲一路走来的不易有着深切体会。池先生本人对于转型做汽配的过程轻描淡写,几句话带过,但是,池宁平记得很多细节,记得过程的艰辛、成功的喜悦。关于这些千回百转的创业历程、转型的阵痛,书里都有体现。再比如,老员工任桂芳,她几十年一直在“利民”,不离不弃一路追随。她跟池先生以及池家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印象深刻的事也挺多,如:池先生家每周的家庭聚会,这个聚会是亲人间情感沟通的桥梁,更是老先生精神传承的纽带。
【3】 关于池幼章与初恋对象叶小姐之间的情感发展描写,占有较大的篇幅和很长的时间跨度,是明线也是暗线,基本贯穿全书。写作手法上,是否偏小说创作?在您看来,他们之间的感情,对池幼章的一生意味着什么?
李:书中大幅度记录池幼章先生的成长经历和感情故事,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池先生生前对这段情感经历十分重视,有特别期待;其次,这些故事展现出了台州百姓生活和社会样态,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第三,这些故事的记录和描写,是文学表现的必须,如此人物性格发展、精神气质养成来龙去脉才清晰,不突兀、不生硬、不造作、不虚假。池先生对叶小姐的深情,几乎伴随一生。意味着什么呢?是温暖、是慰藉、是黑暗中的光亮吧?她是他的心灵伴侣,一直都是——不管是年少时在一起,还是迫于巨大压力分开,乃至后来各自组建家庭生儿育女。长达几十年的岁月,咫尺天涯,让人唏嘘。他们始终在内心为对方留着位置,彼此牵挂彼此祝福却坚守底线,令人感佩。这样的感情自然而纯粹,如橘花洁白无暇,香远益清。
【4】 书中多次写到池幼章自我介绍“我是反革命……”,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年轻人,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长达29年,您每次落笔时是否感同身受,为他的不公遭遇感到压抑憋屈?
李:鲁迅先生说,人类悲欢并不相通。若非亲身经历,的确很难感同身受。时代一粒灰,个人一座山。池先生早年的境遇,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性的幽暗、“运动”的荒唐、命运的冷酷。当我们历经沧桑,知道很多事情并非努力就可以达成,也就学会了接受、懂得了无奈。“我是反革命”,当池幼章一次次自我介绍时,内心是无助而坦荡的。无助是因为无故强加于我的我必须承受;坦荡是因为知道自己没有做错,不管是上学时还是年轻时当文学杂志总编,以及后来做机关工作人员、当老师、办企业等,他都只是一心想着把事情做好。池先生曾经有很多次从政的机会,他都推辞了。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千方百计把企业办好,不辜负改革开放新时代和党的好政策,让员工过上好日子。
【5】 报告文学属于新闻和文学的杂交体裁,写作者需要用沉静的目光、多维的视角、人文的态度来理解,同时以细腻的笔触来表达。请问,写作本书,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李:福斯特说,作家可以作为公正或者不公正的观察者从外部来描写世界,也可以作为无所不在的人从人物内心出发去描写。写作《橘香》,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切换的过程。
【6】 在我看来,本书的叙述风格是安静平和的,内容上却又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20多万字的篇幅,展现了池幼章跌宕起伏的一生,具有相当的延展性和复杂性,写出了大时代背景下人物命运的凛冽感。如果请您写一小段话,作为本书的推介语,您将写下什么?换句话说,您想传递给读者怎样的核心价值观?
李:本书以池幼章先生的成长经历和感情生活为背景,通过一个个故事,再现台州市乃至浙江省近百年来风起云涌的发展历史,揭示了浙商在促进全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你刚提到“延展性”,这个用词很好。我对延展性的理解是指向深远、意蕴丰厚。将池先生86年的人生,幻化在20多万字里面,它是浓缩的,同时又有着特别而丰富的意味,留给读者想象空间。简而言之,他的“我将再起”的壮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继续奋斗”的豪迈,“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的无私,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很好的激励。
【7】 人的命运和生养他的土地息息相关,两者的特征在爱与痛苦之中逐步确立。池幼章一生的际遇一波三折,他的创业史九死一生。本书书名为《橘香》,文中也屡屡写到橘花写到它的幽远馨香,写到它对池幼章人生经历的见证。请问您如何理解池幼章和黄岩这片故土以及他与“利民”的感情?
李:多次写到橘花,是因为池先生的为人处世,也恰似橘花洁白无瑕、温润如玉。黄岩是池先生的故乡,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故乡是中国文学的母题,提供了一个人的基因密码,记录他的成长轨迹。不管作为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人物,故乡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池幼章出身于书香门第,年幼时饱读诗书,种下了文学的种子。还在娘腹时,父亲离家出走,原因不明,行踪不定。他与父亲之间除了割不断的血缘之外,唯一的连接是,父亲曾写信给他母亲,说孩子的名字就叫“池幼章”。这个名字,让池先生认定从未谋面的父亲是爱着自己的——因为父亲叫池瑶璋。说到他与“利民”之间的感情,那肯定不是一个“深”字可以概括,商之大者,为国为民,实业兴国对他而言是深入骨髓的信念,他的企业几经变迁,“利民”二字始终都在。
【8】 跟您探讨一个细节,池幼章曾经卖掉了奔驰车走路上下班,我采访他时,他说那时候人家看他的眼光都不一样了,甚至有人说他,你都破产了还天天去厂里上的是什么班,言语间不无讥讽。我记得池老跟我说,他当时的回答是厂里还有几间老房子我去看看牢。而在《橘香》中,您表达的是,身边从来没有不和谐的声音。我想知道,是池幼章没有提及还是您刻意呈现人性本善。
李:这个,他确实提到过。侧目、讽刺、挖苦不乏其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很多企业家朋友纷纷伸出援手,解决资金问题,而且所有借条都没有写还款日期——他们信任他,认为他有还款能力时,不会欠着不还;他没这个能力时,不应该逼着他。硬币都有两面呢,何况人性。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新闻也好,文学也罢,如何表达如何呈现都是选择的结果。我没有写人家对他的讥讽,主要出于保持基调一致的考虑。
【9】 常言道人生难得一知己。您如何看待池幼章和李书福之间的关系?
李: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他们的认识,应该是注定的缘分。如果当年李书福没有去追池先生的车,如果池先生的车没有慢下来、停下来,让年轻的李书福上了车,他们之间的交集可能要推迟很多年,或许就此别过。几十年来,他们相知相携,跨越很多障碍,历经很多坎坷,迎来企业共同发展。2021年7月15日,在池幼章的追悼会上,李书福的一段发言很能看出他们的相处之道:得知噩耗,顿时陷入无穷的沉思和无尽的悲痛之中。从此之后,再也不能和池老师谈论天下大事、人生趣事、家庭琐事、企业烦事,再也不能分享池老师的闪光智慧、人生哲学。由此可见,他们无话不谈。
【10】 浙江是民营经济发达地区,比起鲁冠球、宗庆后等企业家,池幼章和他的企业相对来说较为普通,在您看来,池幼章靠什么赢得尊重?
李:我们选择尊重一个人,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对三观的认同而产生的尊重,应该是最为持久的。池先生身上有很多特质,如他本人所言既有文学家的形象思维,又有哲学家的逻辑思维,以及“敢于肯定自己,勇于否定自己,善于重塑自己”的大智慧大气魄。他的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他的实事求是、他的仁慈宽厚,所有这些,都是他赢得尊重的基石。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越挫越勇的池幼章晚年重回公众视野,获“风云浙商”“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还上了中国好人榜。采访中,他特别提到2020年9月获得的“最美诚信浙江人”这个荣誉。在他处于低谷时,为啥身边有那么多的支持者?因为诚信。我想,诚信应该是他获得尊重的最大法宝。
【11】 从2021年7月10日至今,已过了9个多月,作为他生命最后3年接触最多的记者,我常常会想到他,每每黯然神伤。我们为他而来,他却缺席了。请您设想一下,如果他还在,对于此书,他会是怎样的读者?
李:他会读得很认真的吧。我想,他那么实事求是的一个人,不会说违心话,可能会提一些不同意见。但总体上估计是满意的——毕竟,我把他的家族史奋斗史创业史,以及他特别珍视的贯穿一生的初恋史,都淋漓尽致地表达到了,没有哗众取宠,也没有遮遮掩掩。
感谢黄岩区委宣传部、李春雷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