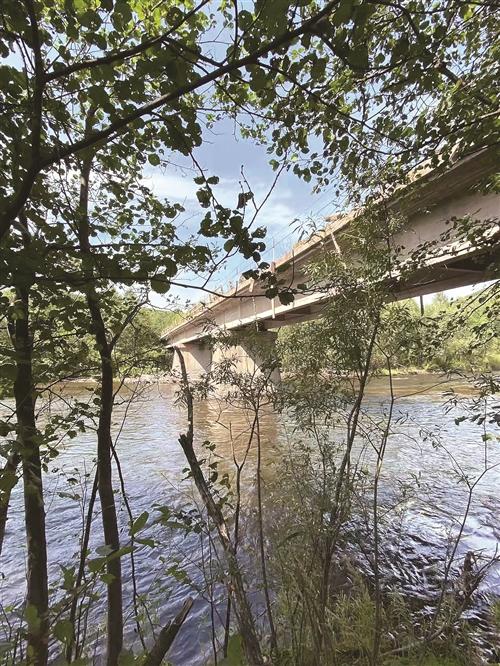本报记者朱玲巧 文/摄
美的本质是什么?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思想家、美学家争论不休。有人却想要给出一个“标准答案”——
2005年起,北大中文论坛的“美学”版块,出现了38个讨论主题,引发了一场长达12年的大讨论,许多知名美学学者、民间高手在此切磋。
帖子的发起者谢良帜,是临海粮食局一个小办事员。他总是戴着厚厚的镜片,穿着白色T恤,过着一种极其朴素的生活,而头脑里却藏着一部百科全书。
60多年苦心自学和钻研,谢良帜提出了关于大脑活动、生物遗传进化、标准和美的本质等新理论。
“我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他执着而坚定地表达对美的理解,光回帖就写了50多万字。
尽管研究备受冷落,但科学贵在探索,无名者的探索本身就值得称赞。
于迷雾中前行,于荒芜处闯荡,逐渐走进新的认识天地,谢良帜说,这就是探索的魅力。
“美是什么”
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美是什么的问题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人类,成了哲学和美学中的著名难题。
对美的本质,美学研究者们提出了形形色色数量可观的见解。
“它们可归成‘只见物’的、‘只见人’的和‘既见物又见人’的三大类。‘只见物’的见解认为美是与意识无关的客观的物,‘只见人’的见解只把美完全归结于人的心灵,而‘既见物又见人’的见解则认为美存在于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之中。”
谢良帜始终觉得,这些还是没有真正撩开美的神秘面纱。
“事唯其难,才能吊起探索者的胃口,才能吸引知难而进者的脚步。”谢良帜踏上了引人入胜的寻美之旅。
在长达30余年的时间里,破解美的本质,几乎主宰了谢良帜的生活。为了寻求一个合理的答案,谢良帜在无数个深夜遍览群书,不断揣摩、独自深思:“美的本质是什么?”
探索的过程有着很难外道的艰辛。走错了方向,纠正过来再走;走进了绝路,就退回到可分路的地方转辟他途。
2005年9月20日,谢良帜写成了《美的本质直解》一文,给出了他的答案,即“美是在人感受事物的过程中事物使人产生愉快的部分”这一定义。
之后,它被修改成更加简练和精准的“美是事物中使人产生愉快的当时的部分”。也可说为“美是使人产生愉快当时的事物中的部分”。
“这应该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定义。”谢良帜说。
2005年10月27日,谢良帜把这个答案,放在北大中文论坛“美学”这一专业子版块上,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12年的大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这个定义虽然不乏诚心的拥护者,但是也饱受质疑、嘲笑,谢良帜一一开门“接招”。
直至2017年9月29日,北大中文论坛关闭,这场“硝烟”才无声地画上了休止符。讨论的结果是,无人能就谢良帜提出的美的定义说出有事实依据的否定意见。
其中最大的争议在于:一个从事非科研工作、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为什么、凭什么那么狂妄,向“美的本质”发起挑战?
对大脑痴迷
1946年1月,谢良帜出生于临海白水洋一个医生家庭。
父亲谢天心曾在白水洋自办诊所,因为医术高超,被方一仁药店聘请。之后又因为从医的成就和名声而被聘为临海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医院升格后,为台州医院中医科主任)。
谢天心酷爱读书。“父亲几乎每个晚上都在油灯盏上点燃三根灯芯,挑灯夜读到深夜。”谢良帜回忆。
“灯火三更长独坐,医家百籍素相亲”是父亲谢天心的人生志向,他一生中除做好医生外,还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并著有《中医四诊辩证与诸病治疗》《伤寒论——药与方的研究》等三部中医学专著。
高中毕业后,谢良帜因出身问题上不了大学,在父亲鼓励下,他开始发愤自学,子承父志主攻大脑生理以及神经生理。
谢良帜对大脑的痴迷始于看到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法后产生的疑问:“大脑世界是怎么样的?”
以前,人们就已发现大脑有分析和综合这两种基本技能,但大脑是怎样产生出这两种技能来的?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他发现,当时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大脑活动,人脑中的细胞——神经元是怎样活动的?是单个活动还是群体活动?
着眼于搞清这些关键问题,他深入研究后认为,人脑就像社会,是有组织地进行活动的,于是提出神经元群理论。
他把神经元群定义为“包含有至少一个基础神经元在内的不同数量的并且相通的神经元集合体”,揭示出神经元群是大脑的机能单位或者说是大脑的基本活动单位。
“产生大脑活动的器官,它的大小只相当于普通瓷碗,但它包罗万象,甚至能装得下宇宙!”
这一理论能解释许多有关的大脑活动现象。它能使著名的条件反射学说中的反射弧,由模糊变得清晰,也在之后解决了美学中一直争论不休的,对动物来说是否有“美”与“美感”的问题。
这一理论是对1891年德国Waldeyer创立的神经元学说的挑战。
这一理论的著述初稿,在1965年5月就完成了。那一年,谢良帜只有19岁,刚离开中学校门不久。
大兴安岭深处的“瓦尔登湖”
就在初踏上探索大脑奥秘征途的时候,谢良帜的人生出现了一个拐口。
1970年11月25日,寒风瑟瑟。临海102名知识青年和大部队会合,乘坐六天六夜的火车,到达了黑龙江大兴安岭支边,谢良帜就是其中之一。
他被分配到黑龙江塔河区盘古镇。白天,在大山深处筑路修桥,晚上回到帐篷,一个帐篷10个人,他掏出自己做的煤油灯,默默坐在角落看书,几乎每晚都到12点后入睡。
1972年,谢良帜完成了系统阐述神经元群理论的论著《论神经元群和大脑活动》。以前草创起来的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三年过去,桥修好了,大部队准备离开。
“你既然那么爱看书,这里刚好缺一个人留守,你就留这儿看书吧。”在领导的安排下,就这样,谢良帜又在大山里独自住了一年。
这里更像是谢良帜的“瓦尔登湖”。一个人的独处,给他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他在大兴安岭深处观察、倾听、感受、学习,日子周而复始,生活简单。
他只觉得如饥似渴,却从未觉得枯燥。这段时间的积累,给他后续一系列横跨多领域的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这期间,谢良帜始终没有把精力从探索大脑的奥秘上移开过。
在此后5年的探索中,他又旁涉了生物遗传进化问题,用自己的理论肯定了历史上一直难以肯定的获得性特征遗传问题,在生物的遗传进化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
大脑世界,很多科学探险者无功而返。谢良帜却是越战越勇。1981年12月,脑研究者对神经元群提出了4点不同看法,这致使谢良帜花了近一年半时间系统地对理论重新推敲。
“我意识到《论神经元群和大脑活动》在叙述上存有欠缺,又写了一篇《神经元群理论简述》。”
科学,就存在于深刻质疑和反复批判之中,发现新问题,作出新假设,确立新理论。
游离在学术界的边缘
谢良帜不是没有尝试过去获得主流学术圈的认可。
从1967年年中开始,谢良帜为神经元群理论,连续不断地与国家有关科研机构、刊物编辑部联系,写去信,寄去论文,希望著述能得以发表。
可是,等来的只有一封封的退稿信。1973年,他把自己有关神经元群理论的研究成果寄给一个权威机构,两年时间,7封来往信件,3次退稿。
“从你所寄来的文章中,我们未能看出国内外有关神经生理等文献总结与自己的实验报告……”
“细胞学说应用于神经组织,早在1891年就有人提出来了……”
他不得不一次次捍卫自己的观点。“科学领域不是任何人的世袭领地。我提出的神经元群理论,与国外的神经元学说在内容、基本思想和所解决的问题等方面都是根本不同的,祖国的科学事业欣欣向荣,我们应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他也曾遇到赏识者。1975年,《中国科学》杂志复信肯定了他的“生物特征获得论”,并赞扬他“对生物学领域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要他把论文压缩到1万字以内,但因信件被人搁置3个月,刊物变革,此事告吹。
上世纪80年代,他又将这些著述汇集在一起交给某科技出版社,但因多种原因也无结果。
其他研究方向也屡屡碰壁——
“美是什么”答案的确立,离不开标准论的研究。“研究‘美的’,关键之一在于认识‘什么样的东西是美的’,那就要在美学中引入标准论。”而当时关于标准论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谢良帜关于标准理论的第一篇论文写于1982年年中,其中关于标准与衡量的理论,可以解决美学中美丑方面的问题。后在“东撞西碰”之中,直至1985年1月9日,此论文才得以在重庆出版的第48期《自学报》上被节录刊登,题为《标准论浅探》。
1988年,在深入研究标准论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反映当时这一理论面貌的论文《标准论论纲》,此论文在内部刊物《台州论坛》1990年第三期上刊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继续对标准论作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到2001年,他完成了《标准论导论》书稿,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标准论。但这部书稿依然几度被搁置。
最新的关于“美是什么”的研究成果,也依然遭遇了不少冷嘲热讽。
“难道从盘古开天辟地至今,天下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美吗?”12年来,论坛中类似的回帖比比皆是。
因为谢良帜在文章中驳斥了罗素的“自然界是无色无光无声无味的”观点,更是引来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不满:“康德、罗素、朱光潜等大咖对美学已有深入的研究,你这不过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言论罢了。”
他将《美的本质》书稿寄给诸多出版社,杳无音讯。
谢良帜不过是无数无名探索者的缩影。很多无名探索者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常人所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的新见常被讥之为狂想;他们的科学探索常被认为是对名家权威的大不敬;他们的开拓精神,反被误解为对科学常识的违背……
这些虽然没有让谢良帜停下探索的脚步,但确实犹如一盆盆冷水,浇透了他的信心。
谢“博士”
在通往科学和真理的探索路上人人自由,但不一定有着相同的结果。
有一天,谢良帜在1989年3月8日的《世界科技译报》上看到美国凯恩斯博士领导的一个课题组研究的最新成果:细菌能够按照某种特定环境选择某种遗传特性,并将这些获得的特征遗传给下一代,由此破解了获得性特征究竟能不能遗传这个谜题。
“这一理论,我在15年前的《论获得和获得的遗传》中就有阐述了!”此论与谢良帜的理论完全吻合,这让他悲喜交集。
他马上给《世界科技译报》写信,请求支持,“为本人,也为国家,争回新理论提出的优先权”。接着,他又与凯恩斯博士联系并寄去论文。凯恩斯博士的信热情洋溢,充分肯定了他的理论,并尊称他为“博士”。
1990年3月14日,《世界科技译报》破例用3个整版介绍谢“博士”的《论获得和获得的遗传》《神经元群理论》和《标准论》。
谢良帜终于迎来了一个等待已久的机会。
1990年6月,学苑出版社开辟了《当代科学前沿探索》丛书,专门为科学前沿的探索者们提供了一个发表自己新见的园地,为活跃在科学领域的改革家们提供了一个争鸣的平台。
《神经元群理论》作为丛书的第一本得以正式出版。
丛书的主编王荣栓教授直言:“神经元群理论所以有这许多年的不幸遭遇,原因恐怕主要在于,这是名不见经传的自学探索者提出的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看待一个理论,应当从它是否有根有据、能否自圆其说,是不是简洁明了、能不能解释现象、与事实相符到何种程度等等方面来判定其是否可取。”
王荣栓认为,“无名探索者的学说是否合理,是否正确,世人有权评说,实践自有验证。以不完善、不成熟为借口,不让其与社会见面,甚至要任其夭折在摇篮里,这总不是对待新学说的好办法。”
《神经元群理论》的出版,让谢良帜得到了久违的认可、鼓舞和鞭策。近年来,陆续有出版社慧眼识珠,《数码国际语》《美的本质》《标准论概论》相继出版。
其中《美的本质》终于遇到了“识珠之人”。有出版社在看完书稿后给出的回复是:“作者得出的这些理论成果,对解决美是什么问题或理解美的本质意义重大。”
“我从来就不是什么‘学者’,而且也没想过要做什么‘学者’。但在科学的殿堂上,应该百家争鸣,平等地商榷,不断探索和创新。”
“如果真要给一个身份。”谢良帜沉吟了几秒后,说道,“就叫我是未知世界的自由探索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