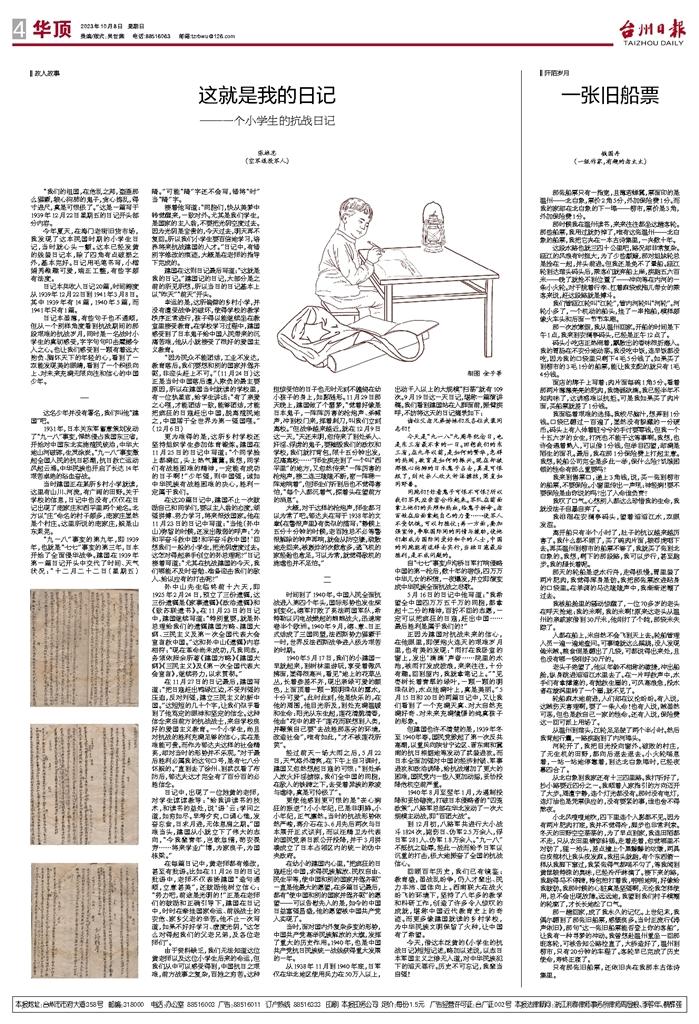钱国丹
(一级作家,有趣的老太太)
那张船票只有一指宽,且薄若蝉翼,票面印的是温州——北白象,票价2角5分,外加保险费1分。而我的家却在北白象的下一埠——柳市,票价是3角,外加保险费1分。
那时候我在温州读书,来来往往都坐这趟客轮。那些船票,我用过就扔掉了,唯有这张温州——北白象的船票,我把它夹在一本古诗集里,一夹数十年。
这段水路也就三四十公里吧,路况却非常复杂。瓯江的风浪有时挺大,为了少些颠簸,那对姐妹轮总是拴在一起,并头前进。但我还是免不了晕船。瓯江轮到达琯头码头后,乘客们就弃船上岸,疾跑五六百米——晚了就抢不到位置了——冲向等在内河的一条小火轮。对于挑着行李、扛着麻袋或拖儿带女的乘客来说,赶这段路就是搏斗。
我们管瓯江轮叫“江轮”,管内河轮叫“河轮”。河轮小多了,一个机动的船头,挂了一串拖船,模样颇像火车头和后面一节节车厢。
那一次放寒假,我从温州回家。开船的时间是下午1点,我来到安澜亭码头,已经是正午12点了。
码头小吃店正热闹着,飘散出的香味很折磨人。我的胃肠在不安分地动荡。我没吃中饭,连早饭都没吃,因为我的口袋里只剩下4毛5分钱了。如果买了到柳市的3毛1分的船票,能让我支配的就只有1毛4分钱。
面店的牌子上写着:肉片面每碗1角5分。看着那两片薄薄亮亮的肥肉,我馋涎欲滴。我已经半年不知肉味了,这诱惑难以抗拒。可是我如果买了肉片面,买船票就差了1分钱。
我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我绞尽脑汁,想弄到1分钱。口袋已翻过一百遍了,显然没有躲藏的一分硬币。码头上有人伸着脏兮兮的手讨要零钱,但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女生,打死也不能干这等事啊。我想,也许会遇着熟人,可以借1分钱,但举目四望,却满是陌生的面孔。最后,我在那1分保险费上打起主意。我想,轮船公司完全是多此一举,保什么险?饥饿困顿的性命有那么重要吗?
我来到售票口,递上3角钱,说,买一张到柳市的船票,不要保险。小窗里传出一声吼:神经病!要不要保险是由你说的吗?出了人命谁负责?
我叹了口气。心想别人都这么珍惜我的生命,我就没法子自暴自弃了。
我徘徊在安澜亭码头,望着滔滔江水,双眼发涩。
离开船只有半个小时了,肚子的抗议越来越厉害了。我什么都不顾了,买了碗肉片面,狼吞虎咽下去。再买温州到柳市的船票不够了,我就买了张到北白象的。我想,剩下的那段路,我可以步行,甚至跑步。我的腿长着呢。
那天的轮船是逆水行舟,走得极慢。胃里装了两片肥肉,我觉得浑身是劲。我把那张票放进贴身的口袋里。在单调的马达隆隆声中,我渐渐迷糊了过去。
我被船舱里的骚动惊醒了,一位70多岁的老头在呼天抢地:我的米啊,我的米啊!原来这老头从温州的亲戚家借到30斤米,他刚打了个盹,那袋米失踪了。
人都在船上,米自然不会飞到天上去。轮船管理人员一遍一遍地查问。可事情就这么蹊跷,没人发现偷米贼。粮食倒是翻出了几袋,可都说得出来处,且也没有哪一袋刚好30斤的。
老头子绝望了,他以年龄不相称的敏捷,冲出船舱,纵身跳进滔滔江水里去了。在一片呼救声中,水手们有拿撑篙的,有抛救生圈的,可风高浪急,投水者在漩涡里转了一个圈,就不见了。
轮船麻木地前进,人们却在议论纷纷。有人说,这贼伤天害理啊,要了一条人命!也有人说,贼虽然可恶,但也是救自己一家的性命。还有人说,保险费这一回可派上用场了。
从温州到琯头,江轮足足驶了两个半小时。然后我背起行囊,一路疾跑到了内河埠头。
河轮开了,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破败的村庄,了无生机的田野,都向后退去退去。小火轮喘息着,一站一站地停靠着,到达北白象埠时,已经夜幕四合了。
从北白象到我家还有十三四里路。我打听好了,抄小路要近四分之一。我顺着人家指引的方向迈开了大步。周遭宁静,连个灯光都没有。那时没有电灯,连灯油也是凭票供应的,没有要紧的事,谁也舍不得熬夜。
小北风嗖嗖地吹,四下里连个人影都不见。因为有两片肥肉打底,我并不觉得冷,脚步也非常利索。冬天的田野空空荡荡的,为了早点到家,我连田陌都不走,只从农田里横穿斜插。走着走着,忽觉哪里不对劲了,猛一抬头,差点撞上个黑黪黪的坟墩,两具白皮棺材让我头皮发麻。我扭头就跑,有个东西箭一样从我脚下窜过,我紧张得气都喘不匀了,等我闻到黄鼠狼特殊的臭味,已经冷汗淋漓了。接下来的路,我跑得马不停蹄,挎包拍打着我,啪啪地响,好像给我鼓劲。我那时候的心脏真是坚强啊,无论我怎样使用,总不会出现故障。远远地,我望到我们村子模糊的轮廓了,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那一趟回家,成了我永久的记忆。上世纪末,我偶尔翻到了那张旧船票,感慨良多。当时正流行《涛声依旧》,那句“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让我有一种寻梦的冲动。我曾想赴温州重坐一回那班客轮,可被告知公路拉直了,大桥造好了,温州到柳市,只有20分钟的车程了。客轮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了。
只有那张旧船票,还依旧夹在我那本古体诗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