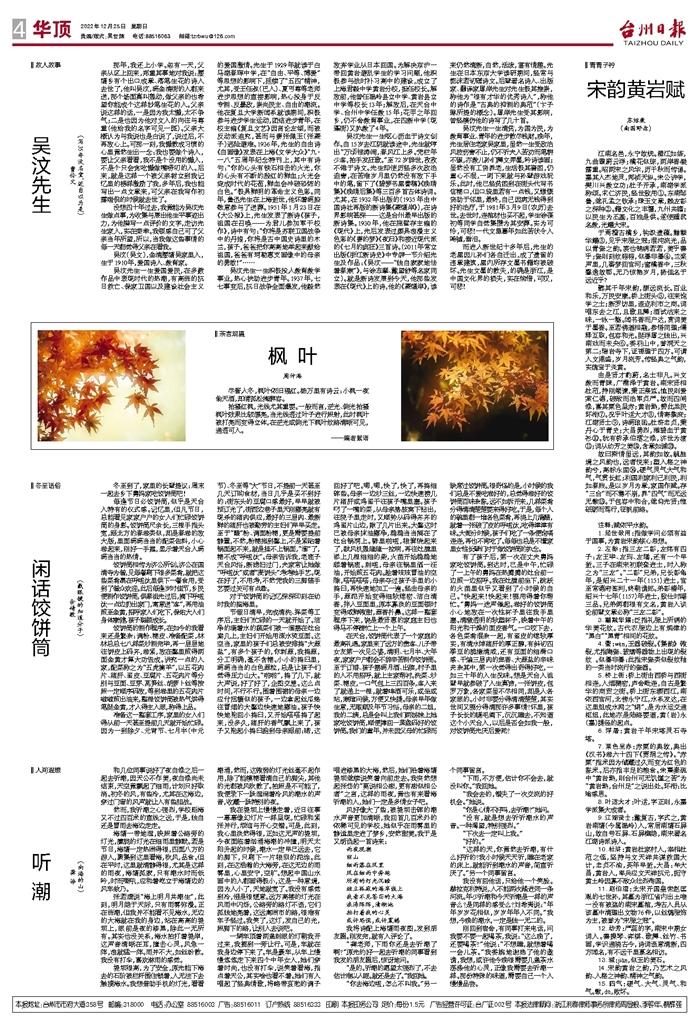那年,我还上小学。忽有一天,父亲从区上回来,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腰塘乡有个出口成章、落笔生花的诗人去世了,他叫吴汶,满金清街的人都来送,那个场面真叫轰动,做父亲的也希望你能成个这样妙笔生花的人。父亲说这样的话,一是因为我太懒,太不争气;二是也因为他对文人的向往与尊重(他给我的名字可见一斑)。父亲大概认为与我说也是白说了,说过后,不再放心上。可那一刻,我懒散成习惯的心里竟然生出一念:我也要做个诗人,要让父亲看看,我不是个没用的懒人,不是个只会贪吃懒做嘴唠叨的人。后来,就是这样一个被父亲树立到我记忆里的榜样激励了我,多年后,我也能写出一点文章来,可父亲在我写作初露端倪的时候就去世了。
没想四十年过去,我竟能为吴汶先生做点事,为收集与展出他生平事迹出力,为他撰写一点评价的文字,走访先生家人,实在荣幸。我顿感自己可了父亲当年所望,所以,当我做这些事情的每一天都觉得父亲在看我。
吴汶(吴文),金清腰塘吴家里人,生于1910年,爱国诗人、教育家。
吴汶先生一生爱国爱民,在多数作品中表现时代的热潮,有高涨的抗日救亡、保家卫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爱国激情。先生于1929年就读于白马湖春晖中学,在“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的影响下,延续了“五四”精神,尤其,受王任叔(巴人)、夏丏尊等老师进步思想的直接影响,热心投身于反专制、反暴政,崇尚民主、自由的潮流。他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期间,积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团结进步青年,在校主编《复旦文艺》因言论左倾,而被反动派追究,甚而与妻张佩玉(张菱子)逃险避难。1936年,先生的自由诗《自画像》发表在上海《文学大众》“九·一八”五周年纪念特刊上,其中有诗句:“你的心头有铁石相击的火光,你的心头有不断的殷红的鲜血;火光会绽成时代的花苞,鲜血会冲破恐怖的白色。”极具鲜明的革命主义色彩。同年,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他怀着满腔敬意参与了送葬。1951年1月23日在《大公报》上,先生发表了新诗《孩子,祖国在召唤——为君儿参加军干校作》,诗中有句:“你将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丹娘,你将是古中国史诗里的木兰,孩子,爸爸把你高高地举起来献给祖国,爸爸有珂勒惠支画像中的母亲的勇敢!”……
吴汶先生一生积极投入教育教学事业,热心扶助进步青年。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毅然放弃学业从日本回国。为解决京沪一带回黄岩避乱学生的学习问题,他积极参与战时补习高中的建设,成立了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担任校长。解放前,他曾任温岭县立中学、黄岩县立中学等校长13年;解放后,在天台中学、台州中学任教15年;花甲之年回乡,仍不舍教育事业,在四新中学(现蓬街)又执教了4年。
吴汶先生一生呕心沥血于诗文创作。自15岁去江阴就读途中,先生就哼出“万顷银涛阔,春风江上多。凭栏年少客,拍手发狂歌。”至72岁辞世,孜孜不倦于诗文。先生即使历经多次政治迫害,在苦难岁月里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留下了《碧箩书屋誊稿》《晚晴集》《晚晴后集》等三百多首古体诗词。尤其,在1932年出版的(1935年由中国诗社再版的新诗集《菱塘岸》),在诗界影响甚深——这是台州最早出版的新诗集。1930年,他在施蜇存主编的《现代》上,先后发表过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妻的梦》《夜归》和接近现代派的《七月的疯狂》三首诗。(2011年常立出版《浙江新诗史》中专辟一节介绍先生及作品:《吴汶——“独自寂寂地怯着春寒”》,与徐志摩、戴望舒等名家同立)。就是新诗发展到今天,他那些发表在《现代》上的诗,他的《菱塘岸》,读来仍然清新,自然,活泼,富有情趣。先生在日本东京大学读研期间,经常与郭沫若切磋诗文。后辈著名诗人、出版家、翻译家屠岸先生对先生极其推崇,称他为“很有才华的优秀诗人”,称他的诗作是“古典的抑制的典范”(卞之琳所提的概念)。屠岸先生受其影响,曾经模仿他的诗写了几十首。
吴汶先生一生清贫,为国为民,为教育事业、青年的进步散尽钱财。晚年,先生居住老家吴家里,虽然一生受政治风波伤害不止,仍不听夫人苦劝而笔耕不辍,亦教儿孙们舞文弄墨,吟诗读画;虽然没有工资养老,生活极其窘困,仍童心不泯,一闲下来就与孙辈游戏玩乐。此时,他已经贫困到在街头代写书信糊口,但口袋里若有一点钱,又慷慨资助于邻里,最终,自己因病无钱得到好的治疗,于1981年3月9日(农历)去世。去世时,连棺材也买不起,学生徐葆初等同学自觉集攒为其安葬。实为可怜,可悲!一代文星暮年如此苦状令人唏嘘,垂泪。
而进入新世纪十多年后,先生的老屋因儿孙们各自迁出,成了遗留的违章建筑,屋内所存文墨书籍均被破坏。先生文墨的散失,的确是浙江,是中国文化界的损失,实在惋惜,可叹,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