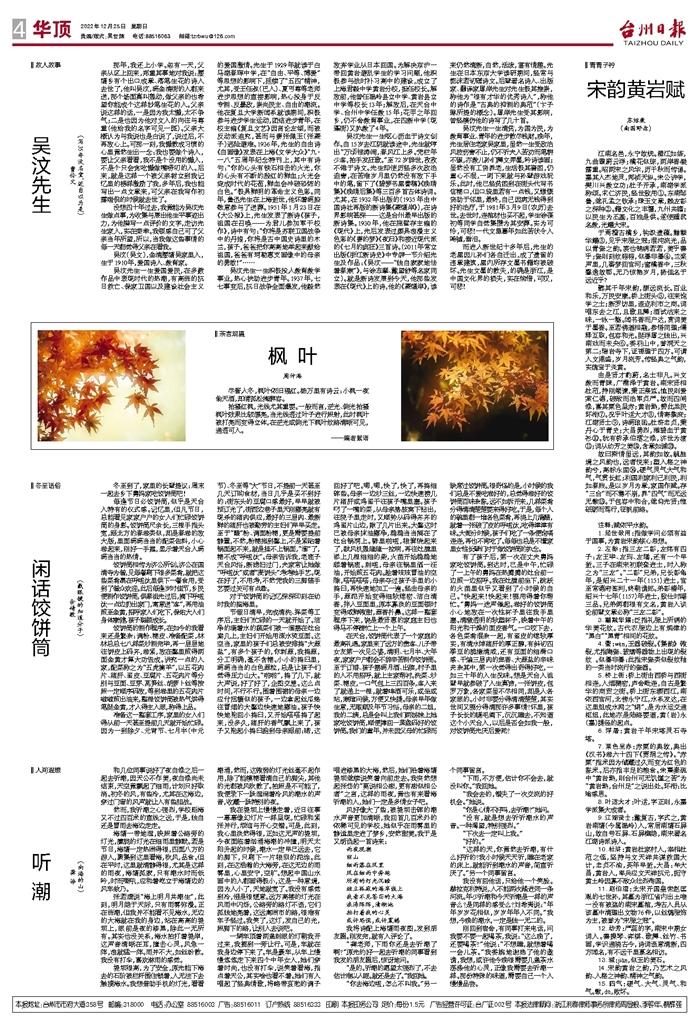和几位同事说好了夜自修之后一起去听潮,因天公不作美,夜自修尚未结束,天空竟飘起了细雨,计划只好取消。初冬的风,有些冷,尤其在这海边,穿过门窗的风声就让人有些胆战。
然而,我听潮之心强烈,学校距海又不过四百米的直线之远,于是,独自还是冒雨去海边走走。
海塘一带地湿,映照着公路旁的灯光,朦胧的灯光在细雨里静默。若是节日,海塘一定热闹得很,四面八方的游人,聚集到这里看海,吹风,品食。但在平时,这里就清静得很,尤其是这样的雨夜,海塘孤寂,只有潮水时而低吟,时而嘶吼,应和着屹立于海塘边的风车欸乃。
张若虚说“海上明月共潮生”,此刻,明月隐于天际,只有雨雾弥漫。正在涨潮,但我并不能看不见海水,无边的大海就在我的身边,站在高高的堤坝上,眼前是夜的漆黑,除此一无所有。其实也没关系,海水拍打着堤岸,这声音清晰在耳,撞击心灵。风急一阵,浪就猛一阵。雨并不大,如丝纷散。我没有打伞,喜欢淋雨的感觉。
堤坝很高,为了安全,原先能下海去的石阶被栏杆围住锁着,人无法下去触摸海水。我想借助手机的灯光,看看潮涌,然而,这微弱的灯光丝毫不起作用,除了能模糊看清自己的脚尖,其他的光都被风吹散了。拍照是不可能了,我便录下一段湿润着冷风的潮水的声音,收藏一段特别的夜。
我在堤坝上慢慢走着,近日往事一幕幕像幻灯片一样呈现,忙碌和紧张并行,烦恼与开心交错。可是,此刻,我心里淡然得很,正如这无声的堤坝,今夜面临着汹涌海潮的冲撞,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潮水一定早已远去,它的脚下,只剩下一片狼狈的泥涂。此刻,在这浩瀚的大海旁,在这无边的雨雾里,心里安宁,空旷。想起中国山水画中的人都画得极小,这是一种意境,因为人小了,天地就宽了。我没有感觉到冷,倒是很惬意。远方高楼的灯光在风雨中闪烁,公路旁的路灯不语,它们孤独地亮着,这远离闹市的路,很难有车子经过。我笑了,这灯,发自己的光,照脚下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一辆车顶着两盏刺眼的灯朝我开过来,我挪到一旁让行。可是,车就在我身边停下来了。车是豪车,从车上慢慢悠悠走下来四个中年女人,她们穿着时尚,也没有打伞,说笑着看海,指点着天公,其实啥也看不着。她们有人唱起了经典情歌,将略带哀愁的调子唱进漆黑的大海,然后,她们沿着海塘堤坝继续说笑着向前走去。我突然想起张岱的“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之言,这样的雨夜,竟也有来看海听潮的人,她们一定是多情女子吧。
风好像大了些,被堤坝击碎的潮水声音更加清晰,我回首几百米外的依稀可见的学校,她似乎在雨雾里的静谧里走进了梦乡,安然甜美。我于是又胡诌起一首诗来:
雨夜观潮
丽山
细雨落在风里
风在细雨中奔跑
所有的灯光沉睡
独立孤寂的海岸线上
我看不见苍茫的大海
浪涛阵阵,清晰地
拍打着我的心灵
或许恐慌,或许震撼
我将诗配上海塘雨夜图,发到朋友圈。刚发完,就有人评论了。
“龚老师,下雨你还是去听潮了啊?”原先约好一起去听潮的同事看到我发的朋友圈后,惊讶地问。
“是的。听潮的愿望太强烈了,不去估计难以入眠。就还是去了。”我回她。
“你去海边啦,怎么不叫我。”另一个同事留言。
“下雨,不方便,估计你不会去,就没叫你。”我回她。
“我会去的,错失了一次交流的好机会。”她说。
“你是心情不好吗,去听潮?”她问。
“没有,就是想去听听潮水的声音。一种渴望,特别强烈。”
“下次去一定叫上我。”
“好的。”
“这样的天,你竟然去听潮,有什么好听的?我小时候天天听,睡在老家的床上,就能听到潮水的声音,简直听厌了。”另一个同事留言。
我没有回他话,只给他一个笑脸。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年少听潮和今天听潮是一样的声音么?是同样的感受么?刘希夷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想,今晚的潮水,一定是独一无二的。
刚回到宿舍,有同事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一起喝茶,我说:“这么晚了,还要喝茶?”他说:“不想睡,就想着喝一会儿茶。”我委婉地谢绝了他的邀请,我想,或许他今晚很需要几盏茶水荡涤他的心灵,正像我需要去听潮一样。那份特殊的味道,需要自己一个人慢慢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