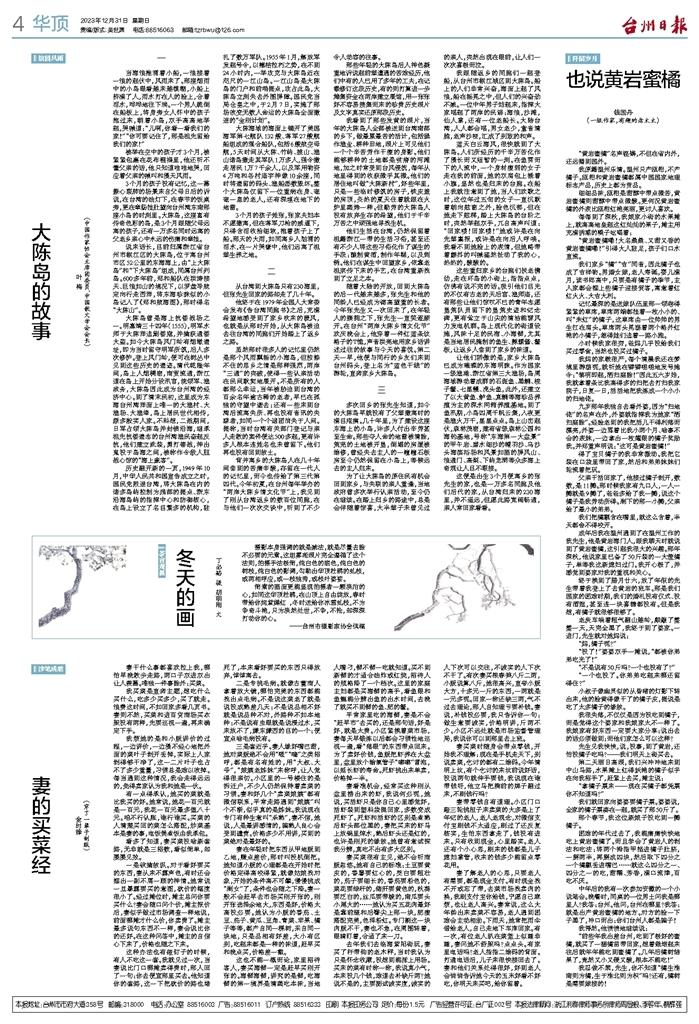钱国丹
(一级作家,有趣的老太太)
“黄岩蜜橘”名声铿锵,不但在省内外,还远播到国外。
我原籍温州乐清。温州只产瓯柑,不产橘子。瓯柑和黄岩蜜橘都属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历史上都为贡品。
细细品味,瓯柑是甜醇中带点微苦,黄岩蜜橘则甜醇中带点微酸。更何况黄岩蜜橘的外表比瓯柑红艳亮丽,更讨人喜欢。
每每到了深秋,我娘家小街的水果摊上,就高高地垒起这红灿灿的果子,摊主用充满诱惑的嗓子吆喝着:
“黄岩蜜橘嘞!大名鼎鼎、又甜又香的黄岩蜜橘嘞!”引得大人驻足,孩子们口水直流。
我们家乡“橘”“吉”同音,因此橘子也成了吉祥物。男婚女嫁,老人寿诞,婴儿满月,读书郎高中,只要是有橘子的季节,主人家都会摆上些橘子迎接贺客,寓意着红红火火、大吉大利。
记忆最深的是送嫁队伍里那一领卷得紧紧的草席,草席两端都挂着一枚小小的、叫“朱红”的橘子,这草席由一位帅帅的男生扛在肩头。草席两头晃荡着两个格外红艳的小橘子,惹得娃们追着一路小跑。
小时候我家很穷,爸妈几乎没给我们买过零食,当然也没买过橘子。
我妈的家教很严,每个清晨我还在梦境里游荡呢,就听她在噼噼啪啪地发号施令:“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因此五六岁始,我就拿着条比我高得多的扫把去打扫我家院子,日复一日,活活地把我炼成一个小小的扫地佬。
九岁那年我独自去看外婆,因为“扫地佬”的名声在外,外婆就指挥我为她家“洒扫庭除”。经验老到的我把活儿干得利落而漂亮,外婆一边骂着比我小两个月、啥事不会的表妹,一边拿出一枚耀眼的橘子奖励我。并郑重声明说:“这可是黄岩蜜橘!”
得了宝贝橘子的我非常激动。我把它装在口袋里带回了家,然后和弟弟妹妹们轮流着把玩。
父亲干活回家了,他接过橘子剥开,数数,是11瓣。那时候我家有九口人,一人一瓣就是9瓣了,爸爸多给了我一瓣,说这个橘子是我劳动所得。剩下的那一小瓣,父亲给了最小的弟弟。
我们把橘瓢含在嘴里,就这么含着,半天都舍不得咬开。
成年后我在温州遇到了在温州工作的我先生,他是黄岩海门人,跟我聊天时就说到了黄岩蜜橘,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那年深秋,他说家里已备了50斤装的一大筐橘子,单等我这新媳妇过门。我开心极了,并感觉到婆家对我的重视和关心。
终于挨到了腊月廿六,放了年假的先生带着我登上了去黄岩的班车。那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我们的婚礼没有仪式、没有酒筵,甚至连一块喜糖都没有。但是我想,有橘子就很够很够了。
老炭车喘着粗气翻山越岭,颠簸了整整一天,天完全黑了,我终于到了婆家。一进门,先生就对她妈说:
“妈,橘子呢?”
“没了!”婆婆双手一摊说,“都被你弟弟吃光了!”
“不是说有50斤吗?一个也没有了?”
“一个也没了。你弟弟吃起来哪还留得住?”
小叔子像幽灵似的从昏暗的灯影下转出来,他的脸黄得像干了的橘子皮,据说是吃了太多橘子的缘故。
我很失落,不仅仅是因为没吃到橘子,而是觉得这个婆家和我娘家太不一样了。我娘家有好东西一定要大家分享;说出去的话必须做到;而他们家怎么可以这样?
先生见我怏怏,说,没事,到了黄岩,还怕没橘子吃吗?——我们明天上街买去。
第二天丽日高照,我们兴冲冲地来到中山马路,水果摊上红得妖艳的橘子似乎在向我招手了,赶紧上去买,摊主说:
“拿橘子票来——现在买橘子都凭票你不知道吗?”
我们就回家向婆婆要橘子票。婆婆说,全家的橘子票凑在一起,就买了那50斤了。
那个春节,我这位新娘子没吃到一瓣橘子。
困难的年代过去了,我能痛痛快快地吃上黄岩蜜橘了。而且学会了黄岩人的剥法和吃法:将两个拇指甲掐进橘子肚脐,一掰两半,再掰成四块,然后取下四分之一个橘瓤丢进嘴巴……就这么四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吃,甜糯、芳香,满口流津,百吃不厌。
中年后的我有一次参加安徽的一个小说笔会。晚餐时,同桌的一位男士问我是哪里人?我答:台州。他问,台州在哪里?我答:就是出产黄岩蜜橘的地方。对方的脸一下子黑了,冲口而出:你们台州人都是骗子!
我愕然。他愤愤地继续说:
“前些年我出差台州,吃到了极好的蜜橘,就买了一捆橘苗带回家,想着栽培起来往后就年年能吃到蜜橘了。几年后橘树结果了,竟然又小又硬又酸,根本不能吃!”
我忍俊不禁,先生,你不知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吗?还有,橘树是需要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