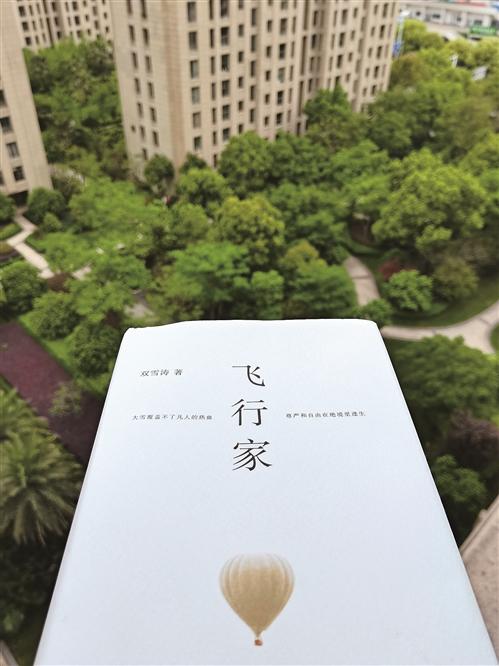林 立
目睹这样的奇人从眼前“飞”走,“我”还能做什么才能平静地度过余生呢?“我”只能成为一个作家,把那些人失落至尘埃里的光彩,用字句垒砌成形。
作家若没有大才,不够狠辣,尤其是对自己不够狠辣,写不了短篇小说。这很微妙,但却是能让人嘴角上扬的事实。
双雪涛的短篇小说,初读冷淡,回味狠辣。
在《刺杀小说家》没改成电影之前,我因为《人物》杂志对双雪涛的报道,买了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我记性很差,情节基本忘了,唯独记住了“双雪涛”这三个字。这名字自此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品质保证。
《飞行家》入手,刚读了双雪涛的自序,就有冲动写篇散文了。
“这个世界如果有人在看小说集,就说明这个世界还没有糟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时值当下,疫情扰乱常态,这句自恋的话是那么可爱。如果不是世界很糟糕,我也不会挤出半个小时,在等妻子哄睡孩子的间歇又拿起小说。
双雪涛短篇小说给予读者的快乐,都标了价码。一口闷完,后劲极大。读完自序,我分三晚读了三篇,《跷跷板》《间距》《飞行家》。
这三篇都是东北故事,我一个南方人,却被逼得想翻开QQ空间扎进过去。过去是不同的过去,但过去时光中的那些脸,都长得很像。
《跷跷板》是我钟爱的双雪涛魔幻现实路子,有刑侦的节奏,有都市男女的呼吸,有严肃文学的架子。对白接近口语,又明显有电影感。故事推进很稳,让我可以保持冷静,但大脑又忍不住想命令眼睛加快速度跑起来。尤其是故事中患癌的“我叔”突然说出惊天秘密那一节,我猛地暂停了阅读,但很快又接着读起来。
读完最后一行,“一无所有”四个字在脑中飘起。我看到一架已经生锈的跷跷板,空着,却自动双向起伏着。我听到起伏时跷跷板因生锈发出的嘎吱声,这声音足以盖过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有热火朝天的轰鸣和那些千篇一律音调高亢的讲话。
好作家,重视的都是被历史书缩略了的那些人的存在。
《间距》特别刺痛我,虽然我并未走上曾向往的电影编剧之路,但零星的剧本创作经历,让小说中四个编剧的身心压力,重重地压了过来。
四人中精神最困顿的编剧,不是第一人称的“我”,而是“疯马”。很显然,这是双雪涛自己经历过的压力,能感觉到他将这部分自我分化成一个“疯马”人物时,是多么轻松、过瘾。这简直是最好的自我催眠、自我治愈。
不过轻松了他自己,就苦了读者。
“疯马”这个才华极高的作家,清醒时烟酒不断,可以为影视公司的任何要求想出绝妙的点子,但也仅限于点子,因为他的能量不允许他停留在那些糟烂的甲方身上。他真正爆发写作能量的时刻,是睡着之后。通过疯狂密集的呓语和足以致人死地的梦游行为,他像一颗会朗诵诗句的太阳一样迸发耀眼的语句。
“我”听到了,却只有听的份,完全无法招架。一个疯了的作家,对亲情、对人生、对世界,有过于纯粹的爱和见解,以至于他除了疯掉,别无与俗世苟合的可能。
“妈妈,我想像花瓣一样一分为二。一瓣给你,照顾你,一瓣给我,想怎么活怎么活。”(《间距》,86页)光是这一句梦呓,就足以让很多读者怆然而涕下。
《飞行家》更加特别,能作为短篇集书名的,是足以概括一本小说集灵魂的作品。小说里的人物,是下岗工人,是双雪涛最中意描摹的那类人。
他们被粗暴地归类于工厂体制内,在体制欣欣向荣时暂且能在时代轨迹上前进,一到下岗潮来临之后,都以不同方式与时代决裂。要说这样的不合群者,有什么地方值得作家将他们的痛苦公之于众,我觉得是“他们的失落”。
有能耐的人,有才华的人,有追求的人,被流水线一样的生活所裹挟。他们或者被边缘化,或者被权力利用。更悲剧的是,他们的至亲,应该唯一懂他们的人,却往往是离他们最远的人。
李明奇这个人物,是《飞行家》故事的中心点。我甚至觉得他是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以来,每一个城市,尤其是县城里,最有代表性的那类普通人。但凡这类人,总是有一些秘闻掌故流传在亲朋之间。他们在黑白的时光里是有颜色的,或许是文艺天才,或许是科技人才,也有些人,只是仪表不凡,总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李明奇指着自己的喇叭裤说,叔,人之身体受之于父母,五脏六腑俩胳膊俩腿不能更换,这衣服却可装卸,所以穿衣服要注意,衣服就是话,穿在身上就是跟人说的一句话。高立宽说,你这行头说的是什么话?李明奇说,说的是,我和你们有些不同。”(《飞行家》,121页)
李明奇这段话,看得我一激灵。我好像没遇到过能说这话的人,但又很熟悉。他们的光彩是一闪而过的,成为普通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大家笑他们的不合时宜,笑他们不脚踏实地。他们的与众不同,是特立独行,是背道而驰。
有创造飞行器理想,并且尝试了大半辈子的下岗工人李明奇,与时代的决裂是如此离奇。在故事的结尾,他如愿“飞走了”,飞得如梦似幻,却让我信以为真。
“我跟你说,人出生,就像从前世跳伞,我们这些人准备再跳一次,重新开始。”(《飞行家》,121页)这是李明奇要“飞”之前,对“我”说的话。这是疯话,可比什么真理都迷人。
他明明对打败自己的生活无能为力,陷入绝望,失落至极,但他对自己折腾的大半生绝不失望。正应了那首被拿来鼓舞大时代中失败者的经典歌曲所唱的,“不过是重头再来”。李明奇就这么干了,决绝而昂扬。
目睹这样的奇人从眼前“飞”走,“我”还能做什么才能平静地度过余生呢?“我”只能成为一个作家,把那些人失落至尘埃里的光彩,用字句垒砌成形。
(摄影:林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