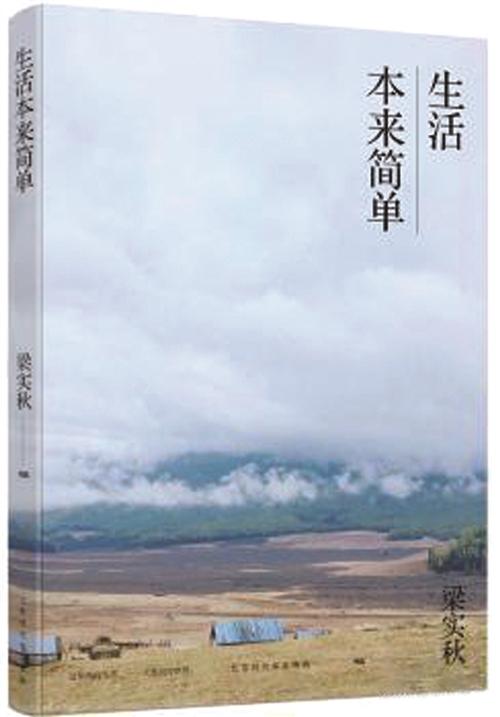范伟锋 /文
“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要去接你”,梁实秋这一经典语段,至今感动着无数人。难怪冰心说: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我曾读过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现又读汇集了他五十余篇散文的《生活本来简单》一书,从中感受到他那浓浓的生活味和不了情,觉得冰心所言不虚。这样天纵英才,实在让人艳羡不已。
梁实秋是地道的北京人。因此,字里行间,北方文化明显,京味儿重。从祭灶、祭祖到办年菜吃饺子、八大胡同打麻将,再去火神庙、白云观、雍和宫人挤人,以及玩九龙斋的大花盒。这京城老式过年在《北京年景》一文中一展无遗;不管《东安市场》金鱼胡同、王府井大街、前门、琉璃厂,还是《读〈中国吃〉》东兴楼、致美楼、厚德福,都将读者带到老北平时光,见到了梁实秋儿时流连的地方;豆汁儿、爆肚、糖葫芦等跃然纸上,只有正宗的本地人才会写好这些地道的特色小吃。
梁实秋认为人类最高理想应是“人人能有闲暇,于必须的工作之余能有闲暇去做人,去享受人的生活”。梁实秋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在他眼里,一草一木,一虫一鱼,皆是生活。光写猫,就有《与动物为友》《白猫王子》《黑猫公主》《猫的故事》《一只野猫》等多篇文章。其他日常如鸟、树、狗,包括海棠、含笑、水仙等花儿,都能进其心、入其文,足见观察入微,柔肠怜悯之情溢于言表。
文人爱吃,远之东坡居士,近则汪曾祺。梁实秋贪吃轶事不断,乐道于美食,也是有名吃货。如写烧鸭(烤鸭),他将制作前后步骤写得一清二楚,“抓住包子的皱褶处猛然提起……轻轻咬破包子皮,把其中的汤汁吸饮下肚,然后再吃包子的空皮”。如此形象生动,足见吃汤包的乐趣,让人垂涎三尺。在《饮膳正要》《读〈媛珊食谱〉》里,梁实秋把天南海北的食材帮派和京城里的名楼风味阐述详尽,读者隔着纸面,即可把美食一网打尽。
尽管梁实秋与鲁迅有过激烈论战,但现实中,梁为人真性情,行文轻松洒脱、幽默风趣,往往于调侃中“留下袅袅的余音”。《骂人的艺术》列出十种骂人技巧,让人忍俊不禁;《戒烟》把自己戒烟的反复写得活灵活现;《房东与房客》则绘声绘色于两者的心态与对话,证明房东与房客关系永远是紧张且离不了。而在《沙发》《狗》等文里,指桑骂槐,诙谐地讽刺了当时社会上某些丑陋,可见其风骨昭昭。
正所谓文如其人。在那个先生辈出的年代,如此味道的梁实秋是这般魅力,在他身上定然有不一样的密码。
梁实秋前半生大陆,后半生台湾,办过刊教过书出过国。他在上海、南京、青岛、重庆等地都待过。一生漂泊的他始终怀念故乡,眷恋祖国。直至晚年,还念叨“但悲不见九州同”。《生活本来简单》里的作品大多是念旧之作。他在《北平的零食小贩》中写“但愿我的记忆不是永远地成为记忆”,在《忆青岛》中写“悬想可以久居之地,乃成为缥缈之乡”。读来,有种物是人非的唏嘘。而这么多的美食名篇,只能解释:居所换了,不变的是儿时味道,还有永远珍藏的乡愁。
能写出如此轻松趣味之作,想来是清澈素净之人。梁实秋照片里的笑容着实感染人。他眼中,“雨有雨的趣,晴有晴的妙,小鸟跳跃啄食,猫狗饱食酣睡,哪一件不令人看了觉得快乐”。他晚年托话给冰心:“我没有变。”冰心听罢,泪如泉涌,回话“我也没有变。”那么不变的是什么呢?一颗简单心而已!
梁实秋行文流畅,无矫情伪饰,少夸张比喻。读其文,犹如听邻家长辈的絮语直白,既亲切又平常。他知识渊博,学富五车,遣词造句信手拈来,给人以水到渠成的自然感。《听戏听戏,不是看戏》把听戏场景、生旦净末丑写绝了,俨然一副正宗京剧票友作派;《群芳小记》写十种花卉,引用大量古诗词和外国诗歌,不由佩服他是文化杂家。
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梁实秋认为“旧的东西之可留恋的地方固然很多,人生之应该日新又新的地方亦复不少”。现实中,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坐井观天,总是睁眼看世界,客观评价中外文明,崇尚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双城记》记录观察台北与西雅图,瑕瑜互见,闻过则喜;《再谈〈中国吃〉》将中餐与西餐进行比较,认为各有千秋,应“虚心地多方研究”。而《养成好习惯》《市容》《圆桌与筷子》则针对那时国人的某些不足,大声疾呼“文明其精神”,体现了拳拳载道心,殷殷报国情。
如今,斯人已逝,贤人作古,空留今人遐想。惟常念先生这句:人的身与心应该都保持清洁,而且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