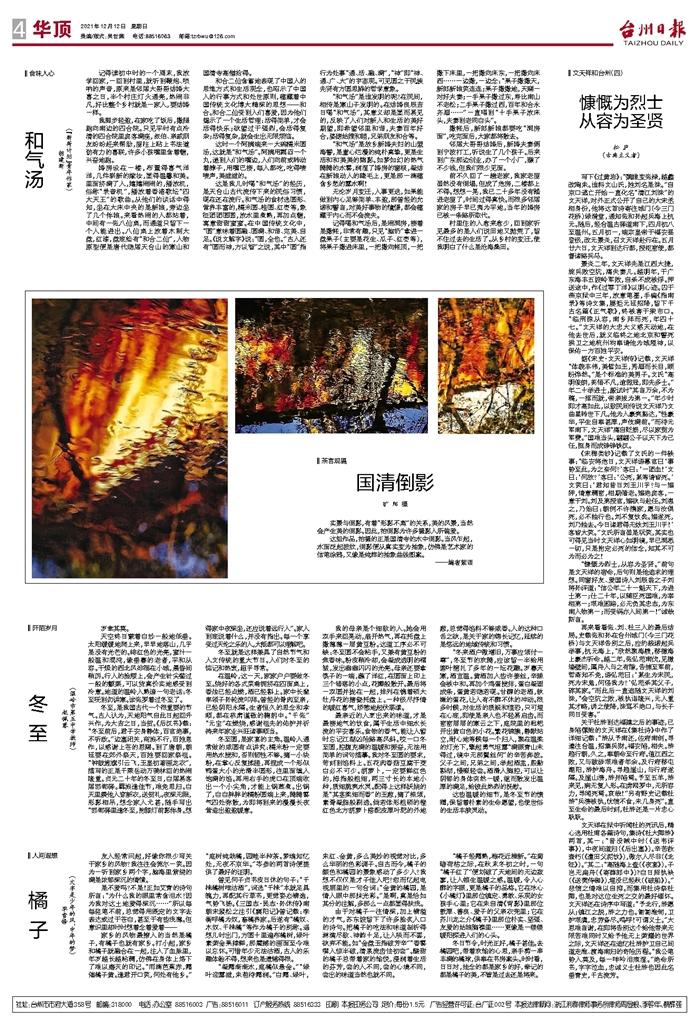写下《过黄岩》:“魏睢变张禄,越蠡改陶朱。谁料文山氏,姓刘名是洙。”自京口逃亡开始一直化名“清江刘洙”的文天祥,对外正式公开了自己的大宋丞相身份,他将这首诗寄往城门(今三门花桥)绿漪堂,通知张和孙起兵海上抗元。随后,经台温古驿道南下,四月初八至温州。五月初一,端宗皇帝于福安县登极,改元景炎,召文天祥赴行在。五月廿六日,文天祥到达行都,授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
景炎二年,文天祥先是江西大捷,旋兵败空坑,痛失妻儿。越明年,于广东海丰五坡岭军败,自杀不成被俘。押送途中,作《过零丁洋》以明心迹。囚于燕京狱中三年,放意笔墨,手编《指南录》等诗文集,屡拒元廷招降,留下千古名篇《正气歌》,终被害于柴市口。“临刑殊从容,南乡拜而死,年四十七。”文天祥的大忠大义感天动地,在他去世后,就义临终之地北京和誓死拱卫之地杭州均奉请他为城隍神,以保佑一方百姓平安。
据《宋史·文天祥传》记载,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是个标准的美男子。文氏“高明俊朗,英悟不凡,逾弱冠,即先多士。”年二十举进士,殿试时“其言万余,不为稿,一挥而就,帝亲拔为第一。”年少时即才高如此,以致民间传说文天祥乃文曲星转世下凡。他为人豪爽豁达,“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而待元军南下,文天祥“痛自贬损,尽以家赀为军费。”国难当头,翩翩公子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成铮铮铁汉。
《宋稗类钞》记载了文氏的一件轶事:“临安将危日,文天祥语幕官曰‘事势至此,为之奈何?’客曰:‘一团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请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刘玉川乎?与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绝宾客,一意于刘。刘及第授官,娼欲与赴任。刘患之,乃绐曰:朝例不许携家,愿与汝俱死,必不独行也。刘不复饮矣。娼遂死,刘乃独去。今日诸君得无效刘玉川乎!’客皆大笑。”文氏所言虽是玩笑,其实也可得见当时文天祥心如明镜,早已洞悉一切,只是抱定必死的信念,知其不可为而必为之!
“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前句是文天祥的宿命,后句则是他追求的理想。同窗好友、爱国诗人刘辰翁之子刘将孙评道:“信公年二十一魁天下,为进士第一;仕二十年,以辅臣死国难,为宰相第一;艰难困踣,必无负其忠志,为东南人物第一;而受祸亦人间第一!”诚哉斯言。
再来看看张、刘、杜三人的最后结局。史载张和孙在台州城门(今三门花桥)与文天祥告别之后,应约践诺起兵举事,抗元海上,“欣然聚海艘,移檄海上豪杰听命。越二年,张弘范南伐,见檄墙壁间,属舟人与之有隙,告捕至军前,哲斋知不免,语弘范曰:‘某生为宋民,死为宋鬼,何怪我为?’弘范杀其父子,碎其家。”而此后一直追随文天祥的刘洙,“会空坑之败,被执诣隆兴,元人重其才略,诱之使降,洙骂不绝口,与长子同日受害。”
关于杜浒到达福建之后的事迹,已身陷缧绁的文天祥在《集杜诗》中作了详细记载:“浒从予南还,佐府南剑。寻遣往台温,招集兵财。福安陷,相失。浒趋行朝,久之,奉朝命至行府。值江西之败,又与跋涉艰难者年余。及行府移屯潮阳,浒护海舟。寻趋崖山,与行府遂隔。及崖山溃,浒并陷焉。予至五羊,浒来见,病无复人形。在虏网罗中,无所容力,寻闻死焉。哀哉!”另有野史记载杜浒“兵溃被执,忧愤不食,未几身死”。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杜浒还是一片忠心耿耿。
文天祥在狱中听闻杜的死讯后,精心选用杜甫各篇诗句,集诗《杜大卿浒》两首,其一:“昔没贼中时(《送韦评事》),中夜间道归(《后出塞》)。辛苦救衰朽(《遭田父泥饮》),微尔人尽非(《北征》)。”其二:“高随海上查(《夜宴》),子岂无扁舟(《寄薛郎中》)?白日照执袂(《送樊侍御》),埋没已经秋(《破船》)。”悲愤之情难以自抑。而集用杜诗祭杜卿,也是对这位生死之交的最好缅怀。文天祥还在诗序中写道:“予北行,浒愿从;镇江之脱,浒之力也。匍匐淮甸,卫护艰虞,忠劳备尽。呜呼!可谓义士。”大恩难言谢,在即将告别这个给他带来无限苦难同时又给予他无上荣耀的世界之际,文天祥还在追忆杜浒护卫自己间道走淮、渡海南归的奇险历程。“我公笔势人莫及,每一呻吟泪痕湿。”绝命所书,字字泣血,忠诚义士杜浒也因此名垂青史,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