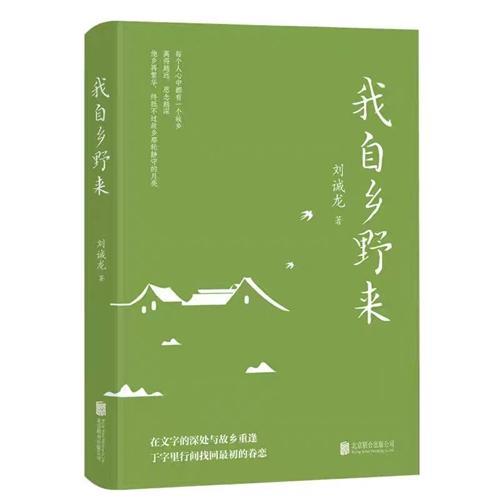赵佩蓉 /文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故乡。这个温柔角落是每个人生命情感的归宿。湖南有个叫“铁炉冲”的村庄,是作家刘诚龙的故乡。鄙陋的乡野,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变成质朴的鲜活的生活场景,成为作者跳出“乡野”之后安顿身心的驿站。以82篇精美散文组成关于故乡的漫长画卷,收拢在《我自乡野来》中。“他乡纵有万盏灯,不抵故乡当头月”,正是作者对故乡的深情告白,同时唤起读者内心深处对故土的思恋。
全书分三辑。“情在情中”,是向记忆追寻乡村真情。亲情是人类最基本最纯粹的情感,予人温暖和力量。《母亲的味道》《母亲的信仰》《翻火》等篇目,一再出现为儿女遮风挡雨的母亲。母亲是作家用心刻划的人物形象,承载着重要意义。作者注重生活细节,对细微又具体的情节进行生动细致地描写,烘托特定氛围,带领读者进入当时的情境。仅文火煎豆腐,先以“洗手、搓掌、蹲身”描写母亲的郑重态度和优雅姿态,再详细叙述动作过程:“身伏炕桌,头倾灶上,摊开一巴掌”,“巴掌上置豆腐块,另一只手操刀”,切成“作业本厚薄”的小块,“小心轻放于锅中”。“一双筷子紧握手中,见边角泛黄,将其夹起翻面,挪置边缘,次第将周边豆腐移至锅中心”。这个细节,不光表现了母亲的动作娴熟,厨艺高超,为子女倾心付出,更是感念母亲在粗糙的生活磨砺中,赐予子女对抗现实的勇气和力量。邻里情是单纯朴素的情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友好相处、互助关爱上。《走毛线的女人》描写冬日阳光下,一堆女人坐在晒谷坪织毛线的事。手里忙着活计,嘴里聊着家常,流露的是对彼此家庭生活的关心和牵挂。邻里间的善意,正是乡村纯朴人际关系的缩影。
“乡在乡中”,是对故乡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诗意表达。故乡的山川草木,鸡鸣狗吠,构成地域的独特印记。信手拈来的物象,充满灵动的生命之美。印象最深的是《对门垄里白鹭飞》。作者对乡间的灵禽施以精致的描写,将白鹭置于“稻田里水光铮亮,黄的稻蔸,绿的水草,黄绿之间,铺陈于漠漠水田上”的优美环境中,耐心地观瞻白鹭的活动:或收敛翅膀,在水田里觅食;或振翅绕着水田飞。天苍苍,树莽莽,草色连天,白鹭划破寂静。无论是目观,还是耳闻,心静,才能垂注并映照苍生。心诚,才能以妙笔表述对自然风物的精纯感知,才能言说“万物皆自得”的生命乐趣,帮助读者重建与自然万物的亲密联系,教会我们领悟乡野间的美好事物。读到这样纯美的语言,借着文字构建充满活力的画面,那种愉悦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
当然,更牵动情思的是带有乡民生活痕迹的一桥一路。时荣桥是一座有故事的老桥。从传说中的神仙帮助建桥,到描述时荣桥边百姓生活的变迁,引领读者走进饱含人情味的乡村。“流水不倦,石桥坚牢”,传达了当地居民坚韧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对乡村朴素的生活美学充满敬意。作者的可贵在于,全方位地看见,诚实地呈现,并不人为添加滤镜,故意美化乡村。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竹子的用处很大,枞树更是抢手货,农家的屋梁,孩子的学费、嫁妆都指望着。生活富裕了,“人都懒了”,“一棵枞树上挂着黑黄黑黄的针叶子”,另一棵“全是光身,光杆杆,一点绿色也没有”。死了的还有竹子。“山可以无人,人不可无山”,倘若少一点人类的贪欲与索求,山林会是独立存在的丰茂的生态系统。舒缓的笔调凝重起来,积压的是对乡村魅力流失的忧虑和遗憾。
“味在味中”,是对故乡美食的重温和传承。对美食的渴望,是人之本能。故乡的食物,并非名馔大菜,都是寻常吃食,联接着乡村贫穷、饥饿的时代印记,却是一剂药引子,牵动游子的相思轴线。吃不完的红薯、萝卜、苦瓜,与时序节令、家庭传统、节日习俗等主要生活事件紧密相连。离开乡村后,作者寄乡愁于美食,不厌其烦地叙写味觉记忆,极其耐心地描绘食物的形貌、制作过程和口舌感受,重新回归到从前乡村生活的缓慢节奏中,上升为思乡怀亲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外皮金黄酥脆内里鲜嫩多汁的炸豆腐,还是米粒清晰可数,清香扑鼻的钵子饭,其背后传递的是因食物建立起来的情感联系,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时空差异下,异地他乡的珍馐佳肴并不能改变顽固的味蕾记忆,丝毫不能动摇作者对故乡吃食一如既往的热爱。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写到,从老家携带土鸡蛋、蔬菜回城,隐含着情感诉求,曲折地表达对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观。
时至今日,这个叫“铁炉冲”的小村庄,可能依然贴着“相对偏远”“欠发达”的标签。感谢《我自山野来》,用散文的形式,让乡村熠熠生辉,让侥幸走出乡野的人,在文字中重回故乡,与天地相见,与真情相拥,与美食相遇,身心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