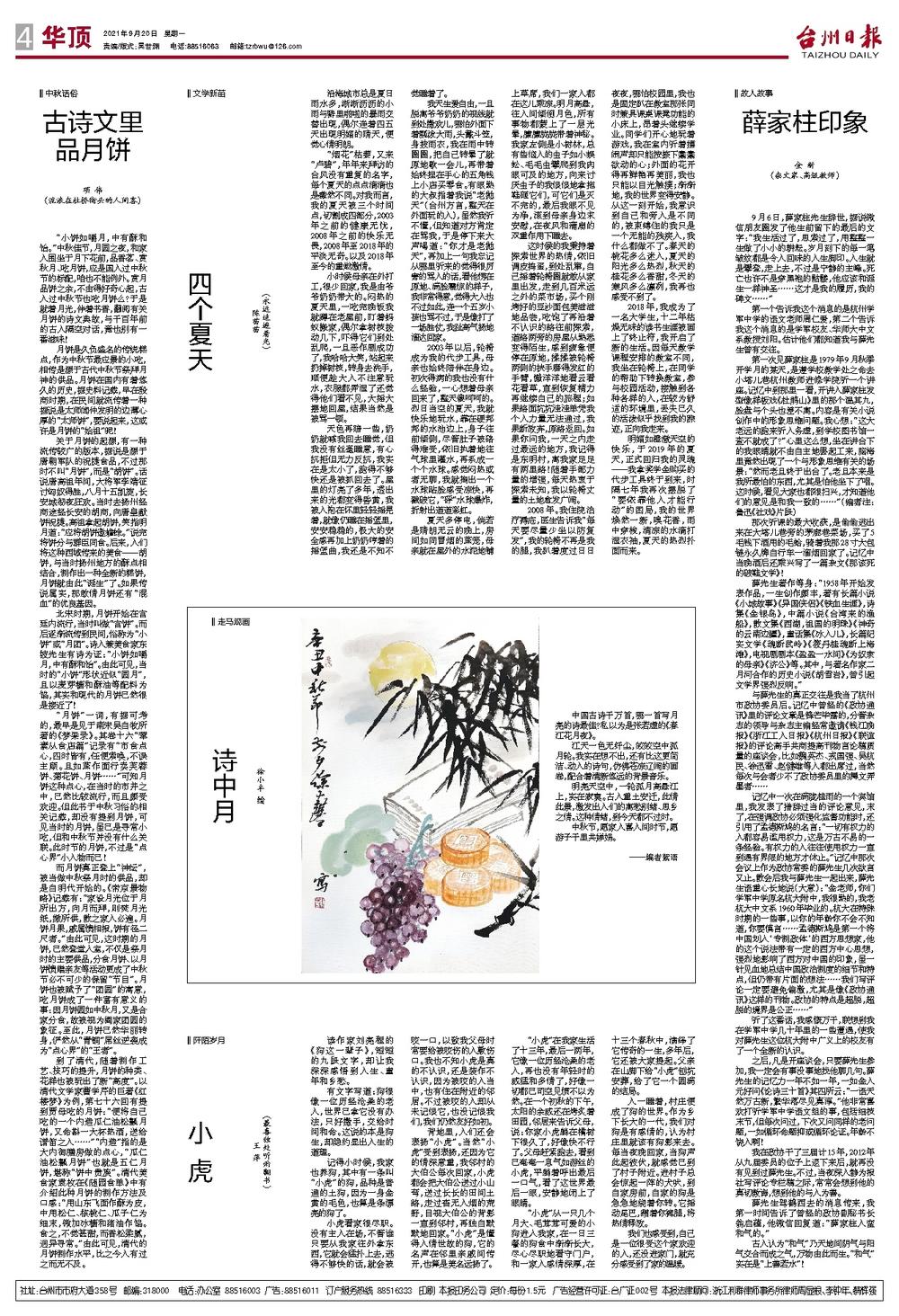沿海城市总是夏日雨水多,淅淅沥沥的小雨与噼里啪啦的暴雨交替出现,偶尔连着四五天出现明媚的晴天,便觉心情明朗。
“烟花”枯萎,又来“卢碧”,年年来拜访的台风没有重复的名字,每个夏天的点点滴滴也是截然不同。对我而言,我的夏天被三个时间点,切割成四部分,2003年之前的健康无忧,2008年之前的快乐无畏,2008年至2018年的平淡无奇。以及2018年至今的重燃激情。
小时候母亲在外打工,很少回家,我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闷热的夏天里,一吃完晚饭我就蹲在老屋前,盯着蚂蚁搬家,偶尔拿树枝拨动几下,吓得它们到处乱爬,一旦恶作剧成功了,我哈哈大笑,站起来扔掉树枝,转身去洗手,顺便趁大人不注意玩水,衣服都弄湿了还觉得他们看不见,大摇大摆地回屋,结果当然是被骂一顿。
天色再暗一些,奶奶就喊我回去睡觉,但我没有丝毫睡意,有心抗拒但无力反抗,我实在是太小了,跑得不够快还是被抓回去了。屋里的灯亮了多年,透出来的光都变得昏黄,我被人抱在怀里轻轻摇晃着,就像仍睡在摇篮里,安安稳稳的,极大的安全感再加上奶奶哼着的摇篮曲,我还是不知不觉睡着了。
我天生爱自由,一旦脱离爷爷奶奶的视线就到处撒欢儿,哪怕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头戴斗笠,身披雨衣,我在雨中转圈圈,把自己转晕了就原地歇一会儿,再带着始终捏在手心的五角钱上小店买零食。有眼熟的大叔指着我说“老抛天”(台州方言,整天在外面玩的人),虽然我听不懂,但知道对方肯定在骂我,于是停下来大声喝道:“你才是老抛天”,再加上一句我忘记从哪里听来的觉得很厉害的骂人的话,看他愣在原地、满脸震惊的样子,我非常得意,觉得大人也不过如此,连一个五岁小孩也骂不过,于是像打了一场胜仗,我趾高气扬地溜达回家。
2003年以后,轮椅成为我的代步工具,母亲也始终陪伴在身边。初次得病的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一心想着母亲回来了,整天傻呵呵的。烈日当空的夏天,我就快乐地玩水,靠在硬邦邦的水池边上,身子往前倾侧,尽管肚子被硌得难受,依旧执着地往气球里灌水,再系成一个个水球。感觉闷热或者无聊,我就掏出一个水球贴脸感受凉快,再戳破它,“砰”水球爆炸,折射出道道彩虹。
夏天多停电,倘若是晴朗无云的晚上,房间如同冒烟的蒸笼,母亲就在屋外的水泥地铺上草席,我们一家人都在这儿乘凉。明月高悬,往人间倾倒月色,所有事物都蒙上了一层光晕,朦朦胧胧带着神秘。我家左侧是小树林,总有些恼人的虫子如小蜈蚣、毛毛虫攀爬到我肉眼可及的地方,向来讨厌虫子的我恨恨地拿拖鞋砸它们,可它们是灭不完的,最后我眼不见为净,滚到母亲身边求安慰,在夜风和蒲扇的双重作用下睡去。
这时候的我秉持着探索世界的热情,依旧调皮捣蛋,到处乱窜,自己摇着轮椅圈就敢从家里出发,走到几百米远之外的菜市场,买个刚烤好的豆沙面包美滋滋地品尝,吃饱了再沿着不认识的路往前探索,道路两旁的房屋从熟悉变得陌生,感到疲惫便停在原地,揉揉被轮椅两侧的扶手磨得发红的手臂,懒洋洋地看云看花看草,直到恢复精力再继续自己的旅程;如果路面坑坑洼洼单凭我个人力量无法通过,我果断放弃,原路返回。如果你问我,一天之内走过最远的地方,我记得是东明村,离我家足足有两里路!随着手部力量的增强,每天热衷于探索未知,我以轮椅丈量的土地愈发广阔。
2008年。我住院治疗褥疮,医生告诉我“每天要尽量少坐以防复发”,我的轮椅不再是我的腿,我趴着度过日日夜夜,哪怕校园里,我也是固定趴在教室那张同时兼具课桌课凳功能的小床上,昂着头继续学业。同学们开心地玩着游戏,我在室内听着嬉闹声却只能按捺下蠢蠢欲动的心;外面的花开得再鲜艳再美丽,我也只能以目光触摸;渐渐地,我的世界变得安静。从这一刻开始,我意识到自己和旁人是不同的,被束缚住的我只是一个无能的残疾人,我什么都做不了。春天的桃花多么迷人,夏天的阳光多么热烈,秋天的桂花多么香甜,冬天的寒风多么凛冽,我再也感受不到了。
2018年,我成为了一名大学生,十二年枯燥无味的读书生涯被画上了终止符,我开启了新的生活。因每天教学课程安排的教室不同,我坐在轮椅上,在同学的帮助下转换教室,参与校园活动,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在较为舒适的环境里,丢失已久的活泼似乎找到我的踪迹,正向我走来。
明媚如澄澈天空的快乐,于2019年的夏天,正式回归我的灵魂——我拿奖学金购买的代步工具终于到来,时隔七年我再次摆脱了“要依靠他人才能行动”的困局,我的世界焕然一新,嗅花香,雨中穿梭,清凉的水滴打湿衣袖,夏天的热烈扑面而来。